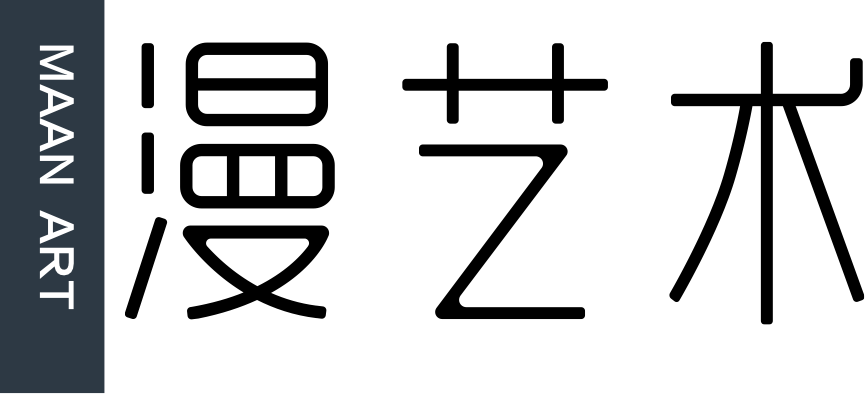洪凌:忆黄山
记者:在黄山的时候您每天都要画画对吗?
洪凌:对,于我来讲,其实画画和吃饭差不多,像每天的日课一样。我们美术学院教学任务不是那种很死板的, 有很大的灵活性,所以大多数的时间教师们还是在完成自己的创作。
我在黄山做这个工作室对于我自己的创作其实是很重要的,随时进入自然,等于是把画室放在山水中间,每天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创作的冲动则源源不断,开启我的心灵。
我每天很简单,早晨起来洗漱完毕,简单吃点早饭, 然后开始在画室发愣。东看看西看看,可能翻翻书,也可能瞧瞧以前的画,然后再想想今天画些什么画。这幅画也许已经完成了一半,或是正在进行中,可能你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在想这件事情,这是连绵不断的一种思维,周而复始地表达和劳作。
画画就像山水的成长、自然的成长,它在你的画布里慢慢弥漫生成,它是一种缓慢的发展过程。有些人看我的画说,洪凌你是不是画得很快啊?一张画如果它气脉上通了,血脉上通了,你就会觉得好像画得很快、很通畅,其实这是一个很艰难的积累过程。有时候你睡觉都会想着这事,想着明天你又要动哪,如何动笔。等你早上到画室来看画时,却常常久久不能动笔,因为你等于又一次进入内心的运化过程,你在看,在想,画布在期待,流程不是事先可以理性设定的。
你在面对大自然的时候,是一种寻找和发现。然后你面对自己的画,其实也是一种寻找和发现,一切都是活体。所以我觉得创作过程很令人兴奋很有意思,你看对象的时候,对象是活的、变化的;而你自己的内心世界也是一个活跃的生命状态,也在变化。二者在变化的过程中寻找一个默契的点。
像我这个年龄,学养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在面对画布的整个寻找过程中,很多经验也会综合进去。那么这个综合加上活跃的体会和观察,就变成一个整体的生命运行。别人看着是树,是草,是山,其实可能是一团一团的气息, 可能是内心一种纠结不清的心绪,通过作品这一精神操作通道,达到生命品质的完成。也就是老子讲的“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生发过程。其实我从中国绘画中吸收营养,就是要找寻中国人自己的表达方式,越来越接近于内心。就像台湾的王德育先生所说的“脱形、随意”。实际上就是从外在一个固化的东西,慢慢进入到一种瞬息万变的内心的影像,一种晃动。由于我在绘画过程中采用的更多的是东方式的表达,这样就给我的绘画表达带来更大的随机性、更大的空间、更大的可以将内心综合进去的可能性。

谷中秋色
布面油画
250 cm x 190 cm
2019
秋光如炬
布面油画
300 cm x 150 cm
2019
记者:所以看着是山水,其实是您的心境?
洪凌:对,所以称为山水画,而不是风景画。中国的山水画和西方的风景画是不一样的。
西方的风景画有大师,可是我们能够数出来的就那几个。西方整体在风景画范围里,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话状态中,内心的那种融入,包括表达的空间、内心的容量,都远远不及中国的山水艺术。
因为中国的山水文化里带有哲学性的思考,同时又辅有诗歌的基础,所以古人观山水时是将其看成生命的一部分。我开始也不太明白,后来慢慢明白了,你看古人画那些山其实就像和尚念经一样是每天必修的,在画山水的同时也是内心的一种修炼。
由于生存的原因,人的内心通常来讲是比较狂躁的,其实人最容易关注的是我们组成的这个社会的状态,西方人的表达长处也在这。西方人长于表达人类,表达人类所形成的这种社会状态、社会关系,而且他们的绘画又擅长于再现,能够很清晰明确地表达一个宏观场景,包括内心世界的一种传递及外在的真实性,这是西方油画所擅长的。当他们面对另一个世界,他们叫作风景,我们叫作山水的时候,通常显得无语或者是说语言不足。因为我们中国从两宋开始,山水的表达就辅以着哲学的根基、诗歌的浸润,加之中国地域复杂、广袤,自然资源丰富,这些都是养育山水文化最基本的条件。庆幸我们民族有这样一个辽阔的山水资源库,有大片的富有变化的、生机勃勃的土地。中华民族跟山水的这种交融、交流与互动,得益于这块非常博大的土地。这块土地养自然,养万物,养山,养树,同时也养人。与自然常年的交流,以致山水的气象血脉已经流到骨子里,渗透到骨髓中, 文化也就是这样养出来的。
夜魂
布面油画
170 cm x 200 cm
2019
记者:您为什么放弃国画转而学西画了呢?
洪凌:因为油画真实啊!那个时候,年轻人大多没有家学,当时所谓的“破四旧”让我们这一代人无家可归。其实中国画很重要的是家学。如果我有家学,如果我从童年一步一步地被引导,家里有中国画,或是学校就给我很完整的中国画的知识的话,让我一步一步地成长,我可能是另一番学习经历。因为中国画需要慢慢地,就像春天细雨蒙蒙沁入土地一样, 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让你慢慢地认识它,逐步地解开它,一开始它不那么清晰,而以后就会一步步柳暗花明。清代“四王”,可能一开始你觉得不好,但是再长几岁你会觉得不一样,再长几岁又不一样。不管你讨厌或喜欢,中国画总是慢慢成长的艺术,而且我觉得中国画更是成熟期的艺术, 甚至它是一辈子的艺术,当你到了老年还可以冲刺。你看中国很多大家, 如黄宾虹、齐白石,都是在年龄非常大了,才达到顶峰。中国画在进入文人画以后,把诗书画放进去,需要的学养非常全面。所以画家越到后来,积累得越厚,学识越渊博,文人画才能达到一定的境界。诗也好,书法也好,印章也好,都能达到相应的高度,并贯通起来,绘画也才得以达到一种通汇老成的境界,孕育在生命中的很多东西也才可以显现出来。所以,中国画是一种到晚年还可以继续冲刺的艺术。
用油画来面对这样的山水文化,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课题。我从西方绘画里提取了这么多年的精华,如何用它的媒材,把这些东西装到中国大文化的口袋里,装到中国山水画这么大的胸怀里,并且能够做到自然地融合,能够做到贴切,做起来慢慢觉得确实是一个大的课题,确实需要几十年,因为这其中需要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保证在这整个过程中接洽的各个端口都做到自然,达到由生命体里流露出来的一种自然状态,包括你的气息血脉,当它们融汇到一起的时候,要拿捏得恰到好处,这是很难的。其实中西这两个大文化,它们是各自在发展,并且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中国画重要的是通其理,解其性。其实中国的绘画观跟哲学有挺大的关系, 你得理解中国人如何面对自然,如何看待自然,如何在面对自然的修炼过程中把内心装进去。行走、思考、体悟、表达是一体的,要求个体生命融入自然万物之中。在表达过程中,去强调哪些部分,滤掉了哪些部分,你得知道、了解才行。油画也是一样,你把油画语言导入另一个系统,你连色彩语言都没过关是不行的,而且另一个庞大的系统从哪里进入最恰当,你得摸到才行。
我现在已基本不写生了,因为以前画了太多太多写生。我觉得有很多很优秀的写生画家画得很好,但是像我这样的绘画,如果真的端着画架子到外面写生,就失掉了综合冥想的空间,这是在中国画里最重要的命题,它需要在画布上长久浸泡着你的思考,积聚着你的智慧, 慢慢地交汇在一起。每一幅画都是在一个统一的精神范围里的显现, 连绵不断地生发着。
四季交响
布面油画
220 cm × 1200 cm
2017
记者:其实您刚刚说到西方绘画也有一套非常严谨的体系,您在绘画早期的时候也花了一些时间来学习和尝试。记得在最开始的时候,您的风格也是有很多种,有人体,也有偏向写实的风景等各种尝试。
洪凌:肯定是的。因为在那个大潮里,在那个时代,中国刚刚把国门打开,西方的文化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我们面对它的时候,就像堤坝打开了,而我们的水非常浅,或者说我们是一个枯水状态,当堤坝整个泻下来以后,我们丢掉了自己,我们放弃了自己曾经达到的如此高的文明,那个时候我们不会回头来看我们的祖先,也没有这个底气,只好在漩涡中各自挣扎。
在那个状态下,我也选择了比较宽的实践面,但我的尝试很短。当时我在美院研修班,美院这个研修班也是旨在为其他院校培养一些年轻师资,那个时候油画专业还没开始研究生班,所以就做了研修班。美院一共办了十届,我有幸在第三届读了两年。
那时候的老先生都非常好,他们敬业,教书也很努力,他们想尽量把自己的东西传授给我们。我们这些学生那时候年龄都比较大,艺术上也比较执着求真、单纯素朴,大家常有交流,那是一个黄金时期。
80 年代中早期是中国艺术探索最好的时期,僵化的思想打开了,我们在寻找着自己的方向,开始做自己的工作。那时我们班里每一个同学其实都蛮有抱负的,蛮有想法的。后来比较有成就的也有,像朝戈,像留学德国的苏笑柏,当时大家都有交流。那时候我们班里都是有家有室的成年人,都放弃了家小跑到北京来,画起来没日没夜,晚上我们还都互相做模特。真是时不再来,留下的都是些珍贵的回忆。
那个时候我很喜欢席勒那种拉长的有点变态的人体,而且我也很喜欢莫迪尼亚尼。所以我的人体作业都比较自觉地做了一些变形的处理,可见那时我对线的造型就比较敏感,有些夸张,情绪上比较苦涩。接着很快毕业了,我就留在学校做了一些抽象的绘画尝试,包括对材料性、肌理层面的追求,但都是纯绘画的,很短。每一个人不一样,那时候我就警惕了,我就想这样走行不行?有些人可能一直走下来,成了很好的抽象表现主义的画家,可能走这条路走得还不错。可我就走不下去,因为它跟我的心性碰不上,我总觉得我需要干的不是这个事,我想我这辈子画这个画得再好,也只会归到抽象表现主义里,是一个抽象表现主义的画家,我想天地应该更宽一点。因为早年学过一点中国画,对中国传 统的东西有一点了解,所以不想在抽象绘画中走下去,其实我心里还是想把中国好的东西拿过来放到一起看看。这是一个个案,当时显得很不入时,没人这么干,还引来很多非议。我想管不住别人的嘴,总能管住自己的手吧!所以没停,干了下来。
记者:您有一幅《野山》,应该是您那个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吧?
洪凌:对,《野山》应该算一个。因为当时有一个中国油画风景展,刚好那时候我已经画了一批实验性质的小幅作品,就说拿出来试试,把一些东西综合起来,一些中国的元素进去以后,确实不一样。也就想在大画上演练一下,看看究竟是不是可行,拿出来也是想给大家看看。
《野山》拿出来,总体的反映还是挺好的。那时候两米乘两米就算大画了,那是我拿出来第一张比较大幅的,算是将东西方两个文化元素碰撞、融合后的结果,也是我个人初步的心得吧。
记者:当时的那个色彩也是比较沉。
洪凌:对,比较沉郁。那个时候都沉郁,总体来讲,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刚刚脱开写实绘画,刚刚脱开 19、20 世纪,对于西方的绘画我们也是很喜欢那种厚重的、浓郁的、朴素的。再说中国绘画基本是黑白嘛,它连颜色都滤掉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画《野山》,我觉得它应该是肃穆的,它应该把油画的色彩弱化,回到一种更浑然的状态。向远了推,接近中国宋代早期绘画的那样一种感觉,是我的初衷。后来到 1991 年的《寒雪》,那时候看画册的时候就一直很喜欢范宽的《溪山行旅图》,还有那个《雪景寒林图》,所以也算是对范宽的致敬吧! 那张画实际上就是奔着北宋去的,宋味十足。那个时候也不像今天我们还会考虑那么多,只是心里单纯地含着敬意,绘画上寻找那种构图和构成方式,然后油画的颜色也是把它压到最底线,深沉、冷峻、幽寒的感觉。那幅画是在北京家里十几平方米的平房里完成的,冬天没有火炉,画得寒彻骨,心气真的接上北宋了。《寒雪》在 1991 年拿出来还得奖了,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所以我在这条路向前走的时候,虽然不断地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在提醒我存在的问题,但是有更多的肯定,让我能有继续的热情。
记者:您刚才说到的就差不多1989年的那个阶段,其实那个时候正是八五美术新潮嘛,当时我们中国很多的艺术家会选择政治波普这样的题材,可是您好像天生对这个政治的题材就没有感觉。
洪凌:是这样的。其实每个人都有热血的时候,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向往平静的生活,但是当你这个民族受到威胁的时候,就匹夫有责嘛,每个人都会拿出自己的热血。从我们打开国门,70 年代末新的一些艺术进来,实际上我的血也很热,年轻人都愿意接受新的东西嘛。而且那个时候我们被禁锢了那么久,我们暗暗都意识到当时的政策是不对的,是错误的,禁锢人的思想,“文革”更不用说,到了极致了,那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少有的。所以在那么一个背景下,早期星星画会点燃的那种激情,那种力争自由的精神态度, 这实际上跟之后的八九现代艺术展,跟整个 80 年代新的文化运动是一起的。
其实中国的新艺术五花八门,新的艺术往往都是以革命的方式开始,着眼于自由,是对艺术形式,更是对现实的突破。西方艺术是一根链条,它不断一链接一链,既包括艺术形式,也包括语言的方式方法,大多提出的是新的文化命题,带来艺术形式语言上的改变。当每根新的链条接起来的时候都是对旧链条的一个反驳,在向前走的时候,西方艺术都以形式革命的方式来向前推进,但多是艺术本体内部生发出的力量。
而在中国,艺术本体改变的诉求大多伴随着政治范围的突破。在当时中国那样的背景下就需要一个更大的力气,甚至呼喊来争自由,所以那个时候政治目的远远大于艺术本身。而西方的艺术变化来自本体,一旦挣脱原有的锁链进入新的链条之时,旧的链条早已完成。西方艺术虽然几年一变,但都会有一批优秀的艺术家在各自的范围里做出非常好的努力和探索,出现一批优秀的作品及有价值的探索。因为在一个新的流派出来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批艺术家已经做了努力,在一个新的力量出来时,原有的艺术其实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艺术探索,干净纯粹。
我们的情况不同,因为西方艺术是一下进来的,是全面覆盖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根本分不出身考虑接受哪些东西,我们为什么接受它,接受它什么。我们常常是只接受了一个形式,然而 形式是空的,你只拿来了一个形式的空壳,那么这个形式你拿来做什么?所以那个时候西方那么多东西涌进来,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们是可以不接受,暂时拒绝不要的,但我们可以选择吗?其中有些东西是硬塞过来的,或者说是我们的浅薄无知、虚荣模仿及剽窃的结果,特别是所谓现代艺术,庞杂多样而无序。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唯西方马首是瞻,认为西方的艺术就是最好的,是自由的范本,但是好的东西不一定都是你的文化精神建设中所需要的。这是从五四以来,中国人养出来的一种固定看法,所以在 70 年代末期那样一个大的环境下,很多人做出这样疯狂的一种举动其实很正常。
其实还有赖于我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我外公也是知识分子,家里留了一点东西,故宫博物院早期送给我外公的《故宫周刊》,我每天看看翻翻,有时也临摹。那时候印刷品没有山水,文化的图像大多是革命政治题材,好多年轻人不知道自己文化的根脉。我虽学油画, 但有幸的是在那个时候就浅显地接触过中国文化,就像现在好多学油画专业的学生以前都对自己的文化有些了解,有的还学习过中国画, 这是由于这些年慢慢在整合回归,整合到现在,逐渐开始正常地面对自己,面对别人。而在我们那个时代完全不是这样的,学油画就是油画, 因为当时那批人大多没有自己文化的基础,全面倒向西方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我当时撤身,跟传统文化的拉动有关,让自己还有一点自己的根基,还包括心性上的一种特别的寄托,反正就鬼使神差地没有往前走了。我觉得艺术不是表面文章刺激眼球,不需要形式花样的翻新, 更重要的是表达语言的真切力量,说自己的话干自己的事,寄托自己的感情,心里踏实。
那个时候在美术学院做纯抽象的表达,还是一个挺新的尝试。当时有一个八人展,我记得还有尚扬、张祖英、何多苓。我那时候拿的作品全是抽象的,反映都各有不同,当时就觉得要拿就拿前卫的、新的艺术。但没多久我就回撤了,所以我说要有一部分回撤的人。我觉得我回撤得比较早,到现在有很多人开始回到中国文化,但我觉得应该回到中国文化深层,它的精神核心上,而不是一些样式。现在很普遍地抄中国画的一些样式,做一些表层的事情。我觉得真正的艺术根本不是表层的,不是表面撕起来的那张皮,而是在画布背后那种深层的人文关怀、人文情结,和艺术家个人的情怀及他生命本身的魅力。石涛讲“黑团团里墨团团,黑墨团中天地宽”,说的是看起来咫尺之间,但是见一个大世界、大天地。这就是为什么书画会让那么多人着迷,会让那么多人把一生托付其中,因为在那里面最终会见到自己的本性,见到自己的心性,求索的过程本身是非常迷人的,非常美的。

丹顶
布面油画
150 cm x 150 cm
2014
记者:那个阶段其实也是您慢慢向黄山,向自然山水间靠拢的一个阶段。
洪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当时我刚刚工作,第一次来到大山大水之间, 第一次来黄山。那时是从杭州坐长途公车,公共汽车很破旧,一路尘土飞扬,从早上 6 点钟到晚上 11 点,颠颠簸簸才到黄山,不像现在两个小时从杭州就到黄山了,所以确实是进步了,但是对山水的那份情我觉得现在的人未必比那个时候的人浓。其实工业化发展越快,反而对山水的认识越浅薄,因为我们更迷恋、更沉醉于工业文明的那种喜悦之中,体验如此快感之后,也会失去许多。
记者:您那个时候看到的黄山跟您之前在北京看到的西山有何不同?南方的山水当时给您的惊喜和冲动是怎样的?
洪凌:是啊,南方的山水在我的视觉感受上是不同的,是全新的。因为在北方也看了一些山,但是北方的山其实比较硬朗,比较干脆,比较挺拔,像碑。南方就是雨雾蒙蒙,山隐藏于植被与云雾之中。山似在非在,它在那儿,你抓不着摸不着。北方的山就在你眼前,容不得你躲闪,直接就过来了。
南方的山像捉迷藏一样,尤其是有烟、有云、有雾的时候。因为在中国南方这个纬度上,一年的降雨量非常大,同时又以土山居多,即使是石头山也含有大量土质,所以植被非常丰富。即使是晴天,许多山谷里的云雾也要到中午才会散去, 所以整个看上去雨雾朦胧,融融的,润润的。这跟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性格也很像,所以老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南方人的朦胧,南方人的细腻和那种暧昧,其实跟山水有直接的关系在我们北方,有时候一醒,睁开眼睛就是一个晴朗的天。明晃晃的,秋风扫落叶,秋天一下就过去了。南方不是,南方缠绵,树上一片叶子黄了, 告诉你秋天来了,缠缠绵绵地要你等到三四个月以后,冬天才不知不觉地来到, 叶子还没掉尽,有时天还暖如春日。这就是南方的细腻,南方的微妙。所以南北两边对山的解读确实不同,对山后面人的解读不同,从山水自然里展现的内蕴与气质都不同。
记者:有一些评价,就是王德育老师也会说您 2000 年之前的作品更有北宋雄伟的那种气势,2000 年以后就更像南宋的那种雅逸, 这个您怎么看?
洪凌:每个人不一样。他们可能没有看到这批画,因为中间有段时间可能是比较淡远的,有一段时间可能会比较接近南宋的韵味。但是这段时间我应该是回到北宋,甚至我都想拉动盛唐的那种精神、那种声音,把那种更强的大美拉动过来。中国绘画其实分两极,一极是由北宋影响带动的,另一极是元的飘逸。因为元以后汉人不大参政,特别是比较有文化的高士们有的出家,有的归隐。但是对自然,他们没有放弃,通过对自然的描绘可以看到他们的心态是放逸的,所以笔墨才得以散淡,才得以放纵,才得以放松。
但是元代的潇洒又是苦闷的,它的秀美里带着一种苍凉,而元毕竟影响了以后中国绘画中放松的一派。至于宋代的绘画则一直影响着另外一条脉络,像龚贤、四王就不说了,再往上明代的绘画如文徵明。其实这两者都在影响着中国两个大的体系。《溪山行旅图》代表宋,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代表着元,元和宋就影响着之后中国各代的画家。
记者:所以您以前的画可能更重气势,现在是更重气韵对不对?
洪凌:对,其实什么时候气要是没了,韵也就散乱了。因为再强壮的气息也一定要有温润在里面,这就是为什么钢不容易断,铁容易断。所以在任何刚强的外表状态下,如果里面没有气在支撑,看上去就很干很涩,很生硬,会让人很不舒服。

太素
布面油画
170 cm x 170 cm
2012

岚岫
布面油画
170 cm x 190 cm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