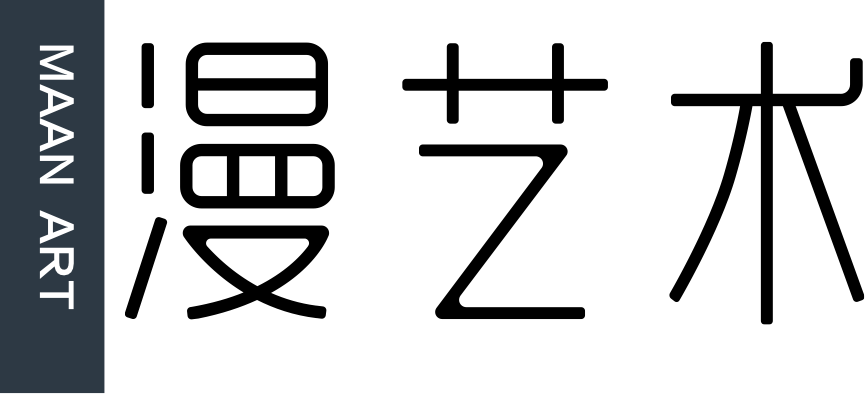◎海洋里的灯台|布上油彩、丙烯、木碳 170cm × 200cm 2023
现实与超越的境域
——寻绎胡志颖艺术之精神
文 - 马少琬
面对胡志颖的作品,习惯于寻求确定的意义、明晰的解读,以及在各个作品之间寻求统一风格的企图,往往会遭遇挫败:从画面形象与标题的题解出发,很难寻绎到往常形式与内容的一一对应;从形式美感出发,也难以获得令人赏心悦目的审美体验。他的作品,似乎处处都在打破我们以往观赏艺术作品的预设期待;处处都在消解我们对于经典符号的惯常印象和固有遗憾的理解。他似乎有意拒绝单一风格的定义,拒绝对确定含义解读的固化,拒绝物象和符号对于思想与内涵按图索骥式地表达。因此,胡志颖的艺术很容易被打上难以理解、晦涩等标签。
◎情侣与图书|布上油彩、丙烯、木碳 200cm × 170cm 2023
◎戏台|布上油彩、丙烯、木碳 200cm × 170cm 2023
然而,真正进入胡志颖的艺术理解的方式之后,就会发现,这正是胡志颖有意为之。具体的形象,容易将关注和思绪引入细节与现实的歧途,而忽略精神性的沉思与超越性的体验本身。而看似复杂、晦涩的画面,指向的反而是最直接的视觉体验,最纯粹的精神追求。那些意义的游移,无法确定、固化的内涵,恰恰试图将我们从现实的虚妄与遮蔽状态中释放出来,指向被我们忽视和遗忘的更为本真的生存与超越的境域。是出于纯粹精神性的追求,对于事物和世界本质的揭示,以及来自对于生存性的直接体验与感知。
将复杂的世界简化,用单一的理论和解释去把握世界,是我们久已存在的偏执和倾向。以便快速把握这个世界,以自己可以理解的方式,实现对于世界的掌控感。然而,这种实用主义的倾向,却不利于对真实的感知。对变化、模糊与不确定的接受,既是对世界本质探索的一部分,也是对内在心灵和精神的超越之境进行探索的前提条件。只有承认混乱、复杂、不确定性,并且只有透过表象与符号的这种性质,我们才有可能接近精神的纯粹、真实。
◎带电的角马和狐狼|布上油彩、丙烯、木碳 200cm × 170cm 2023
◎舞者与猫头鹰|布上油彩、丙烯、木碳 170cm × 200cm 2023
从《舞者与猫头鹰》《带电的角马与狐狼》等作品中,可以看到:色彩、笔触,种种形式带来的冲击与唤醒——冲击,来自对于各种物象符号、文化符号的叠置、颠覆,完全超乎我们的常规经验与文化想象;唤醒,来自笔触的动势,色彩的激荡,形象的震荡,对于内在体验和精神沉思的激发。无论是视觉形象,还是笔触色彩,都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对立与融洽:古典的沉静、典雅,与艺术家个性的自由表达、个体经验的随意转换,出现在同一画面中,非但毫不突兀,反而生发出更有生命力、不为形式所限制的形上意义和精神力量。
◎农场|布上油彩、丙烯、木碳 170cm × 200cm 2023
◎酋长与刺猬|布上油彩、丙烯、木碳 200cm × 170cm 2023
胡志颖的绘画中,不缺乏各个文明中的经典意象,但这些意象又拒绝被以经典的方式解读。因为他关注的并非这些经典的意象本身,他的作品从不是在这一层级上去探讨和表达;而是这些作为文化符号的意象背后的源头,是关于文化起源的原初追问,是个体生存底层的精神动因。
因此,这种对经典文化符号和固有结构的解构,让他可以没有负累地、自由地出入于人类历史和当下世界任一地域的文化资源,打破文明的壁垒与隔阂。因为,在超然和究极的精神探索面前,所有的文化之间的阻隔,都只是经验世界里,有限的、不完整的、暂时性的。既然这些符号本就无关究极与永恒,如何不可随手借用,只要能够稍稍指明通向精神性的永恒道路?
◎欢喜如来之十|布上油彩、丙烯、木碳 200cm × 170cm 2023
◎圣母子与猫头鹰|布上油彩、丙烯、木碳 170cm × 200cm 2019
《欢喜如来之十》《圣母子与猫头鹰》这些明显以宗教为主题的作品也是如此。与其说主题是宗教,不如说是对信仰的追问与思考。相对于绘画史上笼罩于宗教文化的艺术,如教堂壁画,佛教洞窟壁画,文艺复兴雕塑等等,以某一宗教的形象、叙事和教义为主题的艺术作品,胡志颖的绘画所致力于探求的,不是某一具体信仰的阐释,而是对那使得所有信仰得以信仰的信仰本身之求索。不是让自己走进某一种信仰之中,成为其中的信仰者,而是透过信仰的仪式和结构,去观照信仰的神性来源。此前有关宗教和信仰的绘画、雕塑、艺术,乃至于建筑,无不是制造一种具体的信仰,哪怕是进入精神世界,也是引人进入一种有所期待和指向的精神幻境。而不是进入纯粹的、超验的信仰,让信仰本身显现出自身,显现一种更本质、更纯粹的精神性的信仰。这种信仰不只与他人和文化相关,更来自个人生存的需要,是个人灵魂层面的内在体验。
但是,这一超越层面的追求,并不意味着现实世界的事件不重要。相反,对现实世界状况的追问,对个体此时此地生存状态的把握与观照,反而是通向文化的超越层面,通向终极追问的关键途径。他的艺术追求,并不在于具体的现实问题,而是聚焦于精神的超越层面,与生存性的哲学思考。但是,他的观察与思考又从不离开当下与现实。拷问现实与现象的目的,是为了拷问承载这一现实和现象的世界,拷问时刻与这个世界发生关系的自我,拷问我们以何种方式生存于这一世界的存在问题。
◎武士与魁星|布上油彩、丙烯、木碳 200cm × 170cm 2019
◎武士与女兵|布上油彩、丙烯、木碳 200cm × 170cm 2019
因此,胡志颖的装置与行为作品,往往通过对现实世界的关注,从我们现实的境况中发现荒诞,从荒诞的感受中,剥去层层的遮蔽,呈现本质性的真实。以此来重新发现和揭示主体被遮蔽的精神性,达成一种对于文化内在的理解,以及哲学深层的反思。
《后殖民工场》便是这样一种对权力和秩序的诘问:那些艺术品,人类文明中不同阶段、不同地域、不同个体的表达,一个个主体纷繁的思想、创发、想象、激情、灵感的个性化表达,在这里被重新纳入一种观看的权力与秩序之中。在一种许多人视作极为自然、难以察觉的“梳理”中,下意识地,我们的目光对于明晰和秩序的顺从,让观看的对象,指向了这一“文化帝国”宏大的建构,迷失在这一结构里,而忽略了组成这一文化帝国的作品本身。作品自身的独立、饱满、自足、独特的生命特征,被消解于宏大场域的建构。这件作品的形式本身,构成了“后殖民时代”个人处境的一种拟像,看似在普适价值之下各归其位的个人,每个人都有平等的观看、展示的空间权利,每一个人都可以被凝视,但个体灵魂原本拥有的独特性,那些更内在更具超越价值的精神性,那些属于本质生存的东西,却被完全淹没,失去了被凝视、被看到的权利。
◎后殖民工场(03)装置,综合材料,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2019
◎观众在讨论胡志颖的装置《后殖民工场》
这种指向普适价值的形式,反而呈现出自身之荒诞,在现实中的国际政治和当下的社会结构中,不乏其例。《造化之外1》以缺席的圆桌会议座椅,与一架庞大的起重机械并置;原本象征着平等原则和协商精神的圆桌会议,被打破和简化为只有空无一人的残存座椅。面对着强力机械带来的压迫感,文明世界的精神图景与个体生命的存在感知,以缺位的方式,进入到对于世界真实与个体真实的深层反思。
◎造化之外(1)装置,综合材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2018
胡志颖的装置作品中,标题与装置形式,作为两类不同指向的符号,将观者对作品的理解从现实的一端,引向文化底层的自我反诘:标题作为现实的指示性符号,作品作为链接身体与精神的指示性符号,两者的叠加、错位、游移,反而可以造成更为丰富的精神涵义。符号形式与原有语境和意指的悬隔,无法定位与夯实的意义,让作品的内在生命力不断生长、延展,在意涵的深层探索上达到一种意犹未尽之感。《外交辞令》这件作品,其名称尤为清晰地指向当下国际政治的现实,作品由室内向户外、由地下向地面不断延伸,以同一符号的反复叠置,引导观者,在不同的空间中反复地、无意义地穿梭与凝视。作品通过命名和体验,完成一次幽微而又清晰、简洁而又涵泳不尽的文化隐喻。
◎外交辞令(馆内部分)装置,综合材料,纽约Dia博物馆 2017
◎外交辞令(馆背面户外部分)装置,综合材料,纽约Dia博物馆 2017
胡志颖装置作品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媒介的使用与选择。传统创作方式,作品创作媒材,以及作品的展示空间,都建立在具有“空白”“简净”等特点的基材之上,所谓“绘事后素”,如此水墨、色彩、笔触、观念等等才会有充分地游走与表达的空间。当代艺术作品,甚至现成品艺术,也多以单一物质形式来表达,在“白盒子”空间内进行展示。胡志颖的作品却完全突破了这一常规限制。现代社会随处可见的生活物品、工业机械、废弃物,甚至天然动植物、人的日常行为状态,都可以进入艺术的创作。《1+1+…=X》这一作品中,甚至将黑色汽油罐和塑料管,人的匍匐前行等等,与传统中属于“高雅”艺术象征的小提琴等表演艺术并置。
◎1+1+...=X装置和行为(作品全景),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2021
◎1+1+...=X装置和行为,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2021
这种对当前这种变化的世界图景的接受,在接受之上的感知、创作;而不是回到往昔,停留在某一特定的理想之中,这本身就是一种自然美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自然观”的自然美学,同时也透露出一种以生命时间去感知个体与世界的时间观。这种自然美学,包含了对人类社会当下生存状态的接受,面对的不只是自然存在物,也面对后殖民时代、现代与后现代的人的生存境况,面对消费社会与科技文明为人类生存状况带来的种种后果。《几何学冥想》这件作品就体现了这一自然美学——植物,在文明发展的叙事里,一直代表的是一种生命与生机,象征人对自然和世界的链接与流动,与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相关联。人类最初拥有分辨自我、知羞耻,明礼义的智慧,来自一棵智慧树上的果实;释迦牟尼顿悟于一棵菩提树下;孔子讲学于杏树之下。而几何图形,以及它代表的公理演绎体系,是现代文明和科学思维得以立基的出发点。已经步入现代的我们,是否能在科学的真实和生命的真实之间,重新找到一条自由的精神通道,而不是让物质世界的加速追逐,逐渐侵蚀掉个体生命对真实的感知?正如几何指向了对世界秩序来源的终极思考,冥想则指向的同样是对本体和实在等生命真实的感知。
◎几何学冥想(1)装置,树和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修道院分馆 2018
胡志颖作品所呈现的这种释读困境,难以实指造成的多义与歧义,恰恰意味着打开和敞视,意味着通向无限和虚灵之境的可能性。如同轴心时代哲学中的“君子不器”“大器免成”“逍遥无待”,都是在当时文化语境下对既有、定型、刻板的传统文化符号的一种挣脱、打破、重组,并以此接近隐没于精神深处、只能于语言断裂的缝隙处感知的彼岸。胡志颖的探索,让我们看到了艺术精神的自由贯通,对形上世界的精神探索,可以为当下根源性的现实问题,提供一种可能的视角和观照。
◎为什么是蟾蜍?(1)行为装置,综合材料,纽约Dia博物馆 2017.10.15
◎堂吉诃德先生的手电筒装置,综合材料330cm × 330cm × 230cm × 260cm 2017
胡志颖的艺术有一种末世审判的感觉,他在拷问这个世界的同时也拷问着自己。这使得他总是在制造那些冲突性、矛盾性特别突出的图像,但是他从不停留于现实世界具体的现象和事件,而是指向某种根本性的、人的存在的精神远景。虽然他的作品有关宗教性的终极关怀,但是他并非教徒,也不是在创作某种宗教性作品,他并不绝对诚服于某一精神和教义,而是保有一种探究根本性问题的持续热情。胡志颖的世界要足够强大,因为他不依托于任何既有的信仰体系,而是自己编织了这一宏阔而复杂的精神观照系统,并且要倔强地一直走下去。
—— 胡斌
◎图片由艺术家工作室提供|伍锦良摄
Hu Zhiying
胡志颖 -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ANNUAL FILES
艺术家,博士,教授
1987—1990 就读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研究生
1999—2002 就读暨南大学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