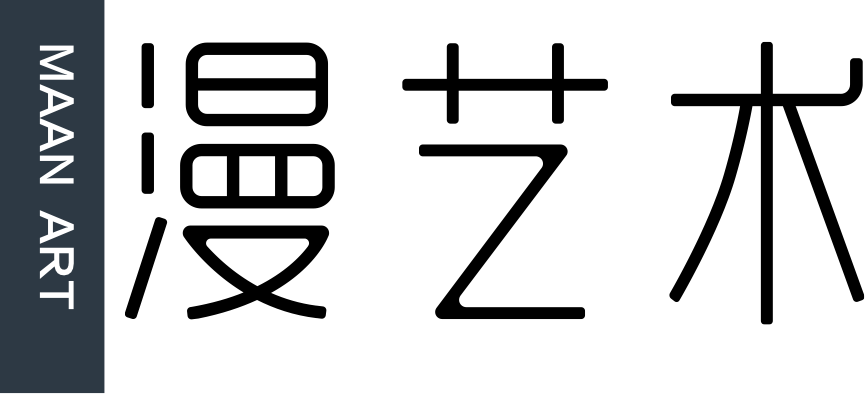陈曦:艺术的温度来自人,而不是机器
本访谈内容同步刊发于《漫艺术》2017年第三辑
封面艺术家陈曦
199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四工作室。
现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造型部。教授、硕士生导师。
陈曦:艺术的温度来自人,而不是机器
采访 _胡少杰
漫艺术= M: 最近看了很多您写的文章,作为一个艺术家,文笔好到让我们写字儿为生的人感到汗颜,如此老到的文笔,背后肯定需要长期的大量的文学阅读来支撑。
陈曦= C: 我对文字可能会讲究一些,虽然多是一些随笔类的文章,但是写的会比较克制,也是受不了煽情的文字。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从小培养的阅读积累,还有我母亲对我严格的文学基础训练,各种中外经典名著在小学时期就读了很多,到了附中时期开始看一些当时比较流行的欧美著作,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在那时以传阅的方式被我看到,印象深刻。大学毕业后开始接触王小波的书,把他的代表作品看了个遍,太爱他的东西了。那几年还有一部是 20世纪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的《兔子三部曲》,也非常喜欢,当然还有卡夫卡、渡边淳一,帕慕克的小说,也都是我偏爱的一些文学作品,我想那是除了叙事情节之外,都还有某种语言自身的表现力带给我的共鸣感。
它世界—5 150x130cm布面油画 2014
它世界—4 150x130cm布面油画 2014
M:这些阅读经验和文学情结对您绘画的影响大吗?
C:当然。那个时期的很多艺术家都有文学情结,包括也受到电影的影响。早年的艺术家这种情结更重,我也还有。作品中出现的叙事性,象征性意味以及情绪,部分算是一种对文学性的视觉化转译。一直到今天,文学和电影为我创作提供营养的方式一直还在产生作用。
M:您最近几年的作品好像明确的叙事性被逐渐地减弱了,绘画中的象征性和隐喻性加强了。应该是从2013年吧,《电视机》系列之后的作品,像《它世界》系列和《物语》系列,转向到了一些个人日常经验的表达之中。这在表达纬度上似乎是一个从向外到向内的转化?
C:我认为是语言面貌上有了变化,而作品中始终关注的内在线索并没有改变。语言确实有一定的更新,因为《电视机》系列已进入了一个绘画表达上的极端,而后我也经过了差不多一年时间的思考和等待,在语言媒介选择的多样性面前,我在考虑绘画上是否还能发掘出新的可能性,后来的某一天,在想要继续实施绘画行为的冲动不可遏制的情况下又开始画新画了。但清醒的是,我不会让肤浅的冲动以及画画的习惯性左右我的开始,我要的是个人独特的经验来再一次推动更自由的表达,绘画是我最熟悉的,也是我最得意的表达方式,但这在今天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选择继续绘画等于宣告选择一种继续保持淳朴的,有人情味的,有人的温度的行为方式来生活,以及保留对生活现实对抗的意图。
木雕和小物件都是我身边最日常的一些东西,而我将它们入画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表现物本身,也无意放大个人小情绪,这里面隐藏的叙述是寓言式的,是象征性的图像。作品里出现的木雕是我收藏的一个德国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有一种很打动我的特质,很质朴,有一点苦涩,又有一点诙谐。但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这种情绪和气质的转移在我的绘画中是明显的,如果你细看的话,一些画面中还隐藏着许多文字和符号,它们可以被辨认出是一些关于社会性的,新闻性的事件信息,或是文学作品中的某个段落,亦或历史中的文明象征性符号,那么这些事件符号与小雕像本没有任何关联,当被并置到一个绘画空间之后就有了某种隐形的联系。其中所有隐喻的社会性问题或人的精神层面的延伸含意就会在语言之外自由的发散开来。画宠物,也是一样的,所指射的都是人的问题,我所忧虑的不是我个人或者某个人群的问题,而是对今天的整个人类精神及行为的某种质疑,所以是个“泛人”的概念。
旅行者 200x110cm布面油画 2014
东边西边 230x146cm布面油画 2014
M:这种在作品中一以贯之地对人的关怀,对社会问题和时代问题的持续关注,这种外化的视野和着眼点似乎和您女性艺术家的身份有些违和?但是反观您在一直以来的创作中似乎并没有刻意地强调女性的身份,但也没有去规避它,您的作品往往既敏感又富有张力,既有女性艺术家中少见的视野和格局又不失感性与细腻。
C:这种说法本身还是一种偏见。在很多人固有的概念里就认为女性艺术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给她预设了一个身份定位。这种偏见和不平等确实一直存在,所以无论是在学术研究上还是市场方面,女性艺术家都是弱势的。前些年我并不太在意这个问题,因为我本人的创作很难看出所谓的女性艺术家特征,这对于我来说也不是什么问题,如你所说,我在作品中不去强调它,也不规避它。我有我个人一直所关注的问题,这个并不会因为我是女性艺术家而改变,我首要关心的不是性别问题,而是整个时代中的所有人的终极命运走向的问题,这可能是我的作品中始终在追问的。但是作为女性群体中的一员,我当然是希望世界上这种基于性别的偏见和不公越来越少。
我觉得作为女性在艺术创作上最大的优势之一是敏感,这种敏感可以是针对个人的内心世界寻找动机和源泉,也可以是针对大时代亦或整个人类的共性问题以艺术的方式进行探讨。作为女性讨论大问题的时候可能更愿意使用柔软一些的,轻松细腻的,不那么严肃的语调去表达严肃的问题吧。
祈祷 210x100cm布面油画 2014
拯救 210x100cm布面油画 2014
M:那么带着女性的敏锐来看待当下的时代,您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什么使您感到焦虑呢?
C:我觉得这个时代的脚步过于太快了。层出不穷的新事物在每天打开手机或电脑时就会跳出来,你如果不能及时去认知它们,一周后就有被时代抛下,与人群隔离开的感受,你被迫接受新技术对生活的强行植入,而这样的改变还会每天更新,若不能适应这样的变化,你就真的会如同身陷荒岛孤身一人。因此每个人都更加忙碌,这样的人生变得缺乏对新事物消化玩味的过程,失去了体会趣味的时间。比如人工智能,现在发展得那么快,但我对这个东西有很重的疑心,我觉得照这样发展下去,人类迟早会被自己的产品干掉的。所以我现在有焦虑,有对人的深度失望情绪,包括对自己的怀疑,我现在会比较悲观。
危机1 145x230cm布面油画 2014
危机2 145x230cm布面油画 2014
M:但是时代的快速发展同样也可以给艺术带来更多新的可能性,因为艺术本身是多元的和自由的。包括面对新的技术,艺术可能会迎来更多的契机?
C:如果艺术创作的全过程都能够让机器代理,那人的价值体现的是萎缩还是被放大?艺术行为还能否强调人的思维、情感痕迹,这些人性的有温度的痕迹。在我看来艺术显现温度感是重要的,作品中显现的观念逻辑和理性分析都不应当失去温度感。而这个温度肯定来自人,而不会来自于机器。即便那是我们所操纵的。我明年 3月份在民生美术馆的这个展览,会有意避开高科技的元素,只用简单质朴的方式去呈现。作为一个个体我们对现实无能为力,我只能试图表露一种质疑潮流的态度。其实面对许多全新的科技发展,我们大多数人是在被动地盲从,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跟着往前走,而真正掌握核心话语权的永远只是少数人,掌握核心技术就是掌握一种生存权利,而如果权利长时间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回看我们的历史,往往这种情况最后的结果都是很可怕的。
半支烟的私语 200x110cm布面油画 2013
男人和玩具手枪 200x110cm布面油画 2013
暗黑 200x110cm布面油画 2015
M:确实,艺术终究还是应该以人为主导。但是即便是绘画这样一种相对单纯的艺术语言,如果在长时间的经验积累之后,是否也会进入某种技术的陷阱里面,或者是一种技术的惯性里面,从而削弱人的主体性?
C:我觉得这种惯性也并非都是陷阱,因为艺术家在长期的创作与积累经验的同时,会形成他独特的个人气质,这种气质总是作品中最容易被人感知到的,也就是个人痕迹。比如像我的作品,无论是《电视机》这种观念性超级写实的作品,还是之前表现主义的,再到今天这些新画,都还是有一种个人一致的气质,而这个气质和语言风格并无太大关系,它是艺术家和作品之间血缘似的一种关系显现。总会很自然地流露于作品之中。
均衡之势 195x150cm布面油画 2015
M:我们这次专题就叫做“圆熟之外”,要说的其实就是这种能够在长期创作积累之后不被技术语言上的圆熟所累,能够始终保持着个人性以及新的创造的可能性。
C:因为我们当年在央美四画室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很自由的学习氛围,完全有别于别的画室的学院式的训练,毕业之后我也是一直保持一种完全自由的创作状态,画画从不追求所谓面面俱到的完美性,很早我就意识到,粗粝的,残缺的,不完整的作品才更具有感染力,也更有生气。所以之前新加坡的蔡斯民先生评价我是“素人画家”,我觉得有道理。这也就形成了这么多年在风格形式上总在变化的趋向,我并不急于形成一个具有高辨识度的个人符号性风格,你可以看到我每个阶段的作品都不一样,我不会停留在某个似乎成功的阶段,因为总有新的问题更吸引我,把我引向下一段,这样听起来好像有点分裂哈,可能因为我在创作以外的很多方面都缺乏某种机智的策略
性。
航母style 150x180cm布面油画 2012
中国记忆之唐山大地震 150x180cm布面油画 2008
M:这其实是艺术家应该有的状态,这种不断地改变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艺术家一个时期的作品一旦积累起来广泛的认可度和辨识度,其实很难再彻底放下,因为这意味着放弃既得的利益,需要甘冒风险。这可能也和您不守成,不安分的性格有关,您这种自由的个性其实也是一种“圆熟之外”,这种个性注定了您一直以一种率直的方式和这个世界相处。
C:其实我也小心地躲开一些真正危险的东西。一些禁忌题材我不会去碰触,因为我还没有那么勇敢。所以我会让自己处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但这并不妨碍我在创作中确立一种独立的精神性表达,来抵御流行病一般的审美潮流。
M:但是能够正视自己的这种无力以及无奈也是一种勇气,而且您也依然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并非只是一个旁观者。
C:我觉得尽量在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基础上,做一些对得起这个世界,也对得起自己的事情,能做的也只有这些。毕竟和很多东西相比,个人很脆弱,不堪一击。
中国记忆之只生一个好 150x180cm布面油画 2010
中国记忆之春节联欢晚会 150x180cm布面油画 2008
M:您在艺术上的终极追求是什么呢?
C:并没有太具体的目标和追求,以前上大学时曾自认为是奔着大师去的,现在世界已然大变,我本身也不是一个喜欢设定结局的人。只是希望能够不断地出新作品,出有价值的作品。把好的状态持久,其他的都不能确定,也不需要确定。艺术上的价值最终是时间和历史来确认的,那不是我的事。
M:下一步创作和展览的计划大概谈谈?
C:最近正在陆续完成几组新的大作品, 2018年 3月份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会有一个新的个展,会展出新的绘画和雕塑作品。
中国记忆之新闻联播首播 130x180cm布面油画 2008
中国记忆之女排在世界舞台 150x180cm布面油画 2007
陈曦版面效果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漫艺术》“圆熟之外”专刊!
MAAN ART
漫艺术
搜索微信公众号:漫艺术,即可快速关注
本周热门
更多- 01 陈文骥:边缘化是我的生存习惯
- 02 谭平 : 从空间里长出来的绘画
- 03 徐冰:艺术从来不是一个时代的光亮
- 04 尹朝阳 : 真正的困境在圆熟之后
- 05 徐累: 普适的内观
- 06 丁立人:我画《西游记》
- 07 沈勤:放逐的诗意
- 08 武艺:内观与旷达
- 09 岳敏君:持续虚无
- 10 尚扬 : 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