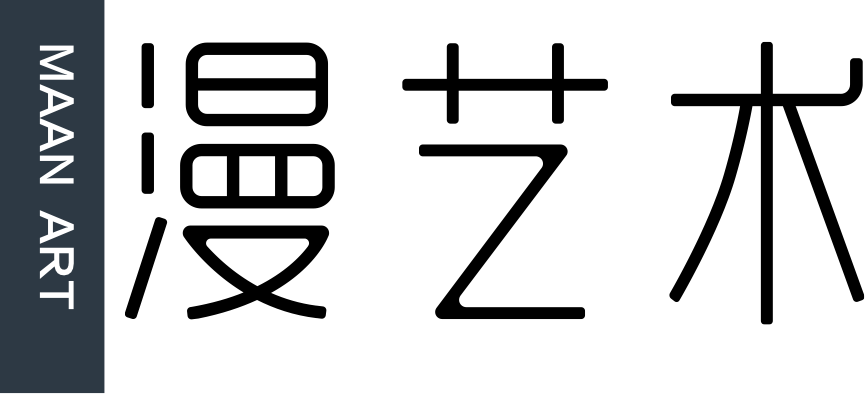段建伟 : 平视的高远
本访谈内容同步刊发于《漫艺术》2017年第三辑
专题艺术家段建伟
1961年出生于河南许昌 ,毕业于河南大学美术系,
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师。
女孩 135×110cm 布面油画 2016
平视的高远
文 _胡少杰
无可否认,艺术只是少数人的事情,但是少数,并不都意味着高贵。
在这个已经被资本、权利、种族、地域,甚至是外貌划分出各种等级的社会,艺术也可悲地成了身份筹码,以至于艺术圈子里待久了的人,会不自觉地产生某种精英感。以艺术的名义谋得资本名望的,自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物质和精神上都自觉高人一等,即便是穷困潦倒的,也满是心理优势,要么自诩救世主,觉得众生皆苦,要么成了自我的精神贵族,觉得众生皆俗。再看作品,或是虚假的悲悯,或是空泛的批判,或是圆熟的避重就轻,大都傲慢、做作、自以为是、自作聪明。缺乏平等的视角,让艺术变得越来越狭隘与浮泛。
水库-1 130×160cm布面油画 2016
水库-2 180×150cm布面油画 2016
段建伟身上没有这种精英感,他在这个充满了伪贵族的圈子里显得不合时宜。在中国当代艺术芜杂的三十几年里,段建伟一直像一个农民对待土地一样对待自己的绘画,无论是八十年代的艺术风潮,还是 2000年之后的艺术商业化大潮,他都一直像是一个置身事外的人。也许是性情使然,在时代的变迁面前,段建伟是一个迟于应变的人,这也印证在了他作品中,在漫长的创作脉络中,你会发现在题材和面貌上并没有过于强烈的变化,而只是围绕着一个艺术母体不断地纯化与深化。这可以反映出段建伟对绘画本身的尊重以及对所画题材的尊重,在他这里你看不到任何策略,一切都是遵从内心的表达,满是诚恳与善意。
少年游 150×180cm布面油画 2010
休息 130x160cm布面油画 2016
批评家习惯于给艺术家分门别类,方法大多时候显得笼统和粗陋,把段建伟仅仅归类为一个乡土艺术家,实在太过短视。而如果我们也按照这个框架来认知段建伟的话,我们必定会错过他百分之九十的价值。当然,近年来也有不少理论家试图给段建伟寻找更堂皇的学理上的脉络和依托,比如本土性,比如西方早期绘画的神圣感等等,这似乎给了段建伟的绘画更高层次的学术价值认定。我不否认这些学术认定的合理性,毕竟外在的艺术史经验对艺术家势必会产生避无可避的影响,如此一来在学术批评的话语系统中也能够帮助艺术家完成艺术语言上的上下文建构,而且在段建伟自己的叙述中一些阶段性和碎片化的认知也能够大概证实这些论断。
扛面 130X160cm布面油画 2013
装土豆 160×130cm布面油画 2016
而除此之外,我认为段建伟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其对这个世界的观看角度,以及和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因为骨子里的质朴和谦逊,在他的绘画中你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傲慢和自作聪明,无论是作品中的人物还是风景,都是以平视的视角来看待,并且给予了最大的尊重,孩童也好,农妇也好,土丘也好,一颗无名的枯树也罢,尽皆如此。因为不掺杂任何先入为主的认知和判断,所以画面不带任何情绪,无论人物的面目,还是四周的山野,都极致的干净,纯澈,而这份滤除一切的纯澈赋予了画面一种亘古的恒久与高远。安宁与静穆,这在我们的绘画中丢失了太久了,我们在段建伟这里找回了这久违的属于绘画的高贵品质,这份高贵来自于平视。
采摘 160×130cm布面油画 2016
唱歌 160×120cm布面油画 2013
两妇女 160×130cm布面油画 2013
红衣女孩 60×50cm布面油画 2014
平视这个世界,平视每一个具体的个体,当然更重要的是平视自己。在这个迷乱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极容易弄丢自己,而只有平视自己才能够看清自己,找回自己。段建伟的绘画在给了我们内心的安宁的同时其实也给了我们许多可贵的提示。在这个人类最迷惑与焦虑的时代,在这个只能靠满足物质欲望才能换得一时廉价的安宁的时代,在这个只能靠虚妄的精神鸦片才能够填补虚无的时代,需要平视自己,平视这个你无从知道是好还是坏的世界,然后看清它,尊重它,抵达它。如此,自然不会再有傲慢,也定然能够放下那虚伪的高贵。
走路 130×160cm布面油画 2011
抱羊 100×80cm布面油画 2014
吹泡 46×54cm布面油画 2013
艺术的温暖旅程
文 _夏季风
作为中国当代一位别开生面的艺术家,段建伟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几乎只专注于绘画这一件事。尽管他的创作发端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与声势浩大的“85美术新潮”运动同步,但他并未追随宏大而喧嚣的波普潮流。当许多同行醉心于新观念以及新材料的实验,迷恋于艺术担当社会政治功能的宣言时,他始终如一,忠实于自己内心纯粹而真实的看法,独自步上了一条孤寂的绘画之路。
段建伟的创作与他的生活经历密切关联,却并没有因此陷入情景重现的写实泥淖。与之相反,他的绘画进入了一种由个人化的自觉性转向形而上化的创作路径。这个过程得益于中国传统艺术中石窟造像和壁画带来的启示,以及他对于文艺复兴早期大师们的深入钻研——尤其是中世纪宗教美术中对人物造像的神圣化、崇高化、永恒化的处理方式,确立了段建伟作品中超越世俗化的现实层面,既凸显了不同于西方以及中国本土绘画的异质性,也呈现出艺术家及其作品中内敛、广博和纯净的精神特质。
传统与个人才能的完美结合,让段建伟具备了当代艺术家中鲜见的历史意识。在他的作品中,不仅感觉到时间的过去性,而且也感觉到它的现在性。既能感觉到绘画艺术传承的整体存在,也能觉察到带有段建伟标识基因的新注入。它们形成了一个共生同存的体系,传递着与这个时代特征相符,却更为复杂的观看方式和更多样的语义。尤为重要的是,段建伟的世界性眼光与民族性结合的创作方法和态度,或许为中国当代艺术日益收窄的绘画之门,给出某种拓展可能的提示。正如 T·S·艾略特所说,历史意识同时会使一个艺术家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他的当代价值。
一直以来,人物是段建伟绘画中的主要对象。准确地说,他的人物就是那些构成乡土中国大多数的农民。在以往众多的创作中,农民的形象很容易被过度化渲染,艺术家通常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视角在看待这个阶层,要么高大上地颂扬,要么居高临下地怜悯。而段建伟的创作态度似乎介于这两者之间,甚至就像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以平和对等的眼光去打量着身边的人与事:劳作,憩息,喜怒哀乐,甚至无可名状的苦恼。对农民世俗化的日常生活的描摹,事实上也是艺术家展现了同样栖居在大地上的其他人的普遍性行为。农民既是农民,又是他人,也是艺术家本人。万物皆有灵性,与其说段建伟在画农民,不如说是对生命本质的感悟与赞美。他对人性内在的、深邃的探究和关注,让他的作品重现了本雅明所说的“在机械复制时代凋萎的灵晕”。
具备灵晕的作品正如一个拥有灵魂的人,总会让人感到温暖,亲切,不那么冷漠。这也是优秀艺术品理应具备的品质。段建伟的作品总是让人感受到艺术家倾注其中的灵魂和温度,经他之笔创造的那些人物,仿佛在作品完成后能觉察到自身的存在,内心的满足和感恩洋溢于表。好作品向来如此:它不仅独立行走在这个世界,同时还会传递和分享艺术家赋予它的一切,带领我们共同踏上艺术的温暖旅程。
艺术家在工作室
段建伟版面效果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漫艺术》“圆熟之外”专刊!
本周热门
更多- 01 陈文骥:边缘化是我的生存习惯
- 02 谭平 : 从空间里长出来的绘画
- 03 徐冰:艺术从来不是一个时代的光亮
- 04 尹朝阳 : 真正的困境在圆熟之后
- 05 徐累: 普适的内观
- 06 丁立人:我画《西游记》
- 07 沈勤:放逐的诗意
- 08 武艺:内观与旷达
- 09 岳敏君:持续虚无
- 10 尚扬 : 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