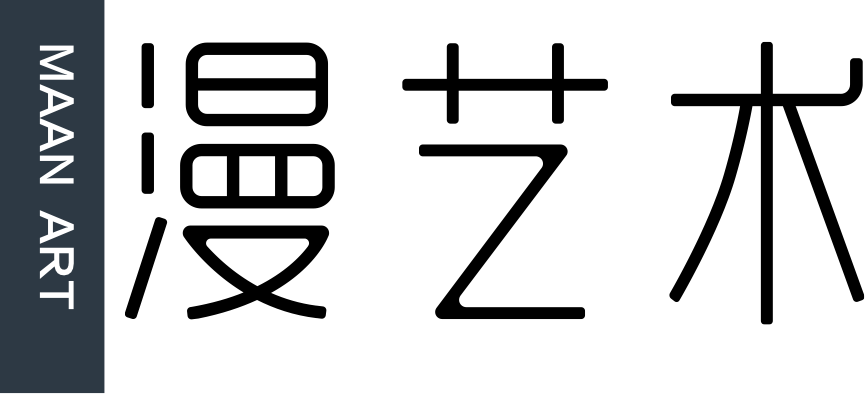谭根雄:通向一种交互主体式的表现主义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漫艺术》杂志2018年5月新刊
专题艺术家谭根雄
1956 年出生于上海
1983 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
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观念·形态艺术工作室日常主持人
通向一种交互主体式的表现主义
读谭根雄《黑雨系列》
文 _ 薛学材
2016 年 3 月 18 日,临近春分,小雨淅沥,谭根雄《黑雨系列》在福建省美术馆开展。据悉这是《黑雨系列》首次完整展出。甫一进馆,大感天气骤变,馆外清爽的小雨瞬间化作压城的黑云。与此相应,忍不住在心头暗呼一声“谭根雄又变了”!
是的,谭根雄又变了;从早期的写实到《紫禁城系列》的抽象是一变,而《黑雨系列》写实与抽象相交融似乎又是一变。不过,个人印迹还是清晰。支撑谭根雄油画的两大支柱:“历史意识和雄浑笔触”依旧在眼前的《黑雨系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不过呈现观念的视角和手法已经与往昔颇不相同。
黑雨系列#150 100cmx120cm布面油画 2013
黑雨系列#151 100cmx120cm 布面油画 2013
一、作为批判手段的历史意识
纵观谭根雄的创作历程,历史意识可以视为谭氏绘画一以贯之的核心。谭根雄的艺术手法是多变的,早期作品以严谨的具象写实为主,九零年代后期至今则多在抽象表现方面苦心探索,但历史意识始终是谭根雄最为重要的表现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将历史意识视为谭根雄艺术意志的主要来源。
有必要强调一点,我们不应该将历史意识等同于历史题材,有许多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在历史意识方面几乎等于零。所谓历史意识,可以较为简单的定义为“人们在历史认知基础上凝聚、升华而成的经验性心理、思维、观念和精神状态”,换言之,即对历史的意识。就艺术来说,历史意识并不一定要在历史题材中表现,而历史题材则可表现出不同的历史意识。至于历史意识的不同类型,尼采分为纪念的、怀古的和批判的三种。尼采说:“历史对于活着的人而言是必需的,这表现在三方面:分别与他的行动与斗争、他的保守主义和虔敬、他的痛苦和被解救的欲望有关。这三种关系分别对应了三种历史,要是它们能被区分开的话:纪念的、怀古的和批判的。”
就个人或具体艺术作品而言,所具有的历史意识通常是比较复杂的,很难明确地指认为三种中的哪一种,更多的时候是复合的。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可以努力去辨认出其中的主要成分。谭根雄作品中的历史意识,我认为主要是批判的。这在他的抽象作品中应该是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不过,在他的具象作品中同样也蕴藏着批判的历史意识。以参加第九届全国美展的《胜利者》为例,此作题名指向“人”,似乎暗示这是一幅纪念式的历史画。但当我们直面画作时,却有一些异样的感觉。《胜利者》几乎没有背景和景深,画作的主体由一位战士和一架大炮构成;大炮以局部特写的方式占据了整块画布,而战士被安排右半部分。尽管喜悦通过面容上隐约的微笑得到充分的表现,但消瘦的脸部疲倦的神态同样清晰,这与正统的以赞颂英雄为主题的革命历史题材绘画颇有差别。实际上在《胜利者》中特写的大炮在视觉上的吸引力完全超过战士。炮架的转轮及其他零部件以极为厚重细腻的笔触精心描绘,使这一幅画将观者的注意力无形中引向了对战争和历史的思考,而不仅仅只是纪念一场胜利。作者的另一幅作品《解放者》也与此作相似,画面中六位战士手持武器,但作者却没有画出战士的眼神,神态也并不昂扬,这意味着作者所表现的重点不是人物,而是事件;主要的目的不在于纪念和赞颂,而在于引起反思。也就是说这两幅作品表现出的历史意识主要是批判式的,而非纪念式的。这是谭根雄历史题材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
紫禁城#305 100cmx80cm 综合材料 2004
紫禁城#304 100cmx80cm 综合材料 2005
批判式的历史意识在谭根雄的抽象画代表作《紫禁城系列》中发展到了顶峰。我们无法从视觉上辨识这些画的内容,只能看出层层叠叠的颜料交织出凝重繁复的色彩,还有在色块之上力道十足稍显狂乱的粗砺线条。唯一提示我们画中物质实体可能是城墙的就是题名。作者将这一系列抽象画命名为《紫禁城》而非“故宫”,暗示他所画的是过去,或者更准确的说是站在当前所可能看到的过去的中国,即历史。这历史由于融合在现实的视野中而显得模糊不清。它是我们视野的起点,同时又干扰我们的视野;它给我们慰藉,同时也让我们焦虑。反复覆盖的颜料营造出的纵深感暗示了时间漫长,雄浑厚重的笔触呈现出的混沌感则暗示了关于历史的困惑。“紫禁城”无疑属于具有巫鸿所谓的“纪念碑性”特征的建筑,对于此种“纪念碑性”美学特征的绘画表现应该是清晰的、庄重的、和谐的,比如郭仁杰的《故宫系列》。谭根雄《紫禁城系列》的抽象形式则是反“纪念碑性”的,它引导观者在思想中撕开繁复混沌的形式,去思考历史的真正内核。
该谈谈《黑雨系列》了。据画家在开幕式上的介绍,这一系列的创作时长延续了十多年。《黑雨系列》共 37 幅作品,除了主题索引《救赎》和章节提示《柏林墙》(之一、之二)三幅是彩色的外,其余皆以黑白为主色调,局部施以红色。与《紫禁城系列》的抽象主义风格不同,《黑雨系列》回归具象表现,在保留了一些抽象绘画构思特点的同时(主要是背景和色调),更多出了许多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在这些作品中谭根雄似乎企图在具象与抽象之间寻找一种平衡。
在长达 6 米展览主题索引画《救赎》中,画家以抽象的方式暗示《黑雨系列》可按照一定的逻辑分为五个版块。在我看来,这其中蕴含了画家对历史的思考。与谭根雄以往的作品相比,《黑雨系列》显示出的视野更加宽阔,意识更加深刻,力图表现的主题也更加复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作品展示了谭根雄艺术意志中对史诗品格的追求。《黑雨系列》的历史意识仍然以中国为基点,但并不局限于中国,而是进一步扩展到对人类总体命运的思索。在三十多幅作品中,那些穿着带有梅花、喜鹊、童子等图案的衣服的婴儿似乎指向“传统中国”;那些五星红旗、雷锋、切·格瓦拉头像等生活场景装饰明显指向“革命中国”;那些迈克尔·杰克逊、艳舞女郎似乎指向“改革中国”;那些飞机、导弹的超现实战争场面无疑指向全球化过程中潜藏的“国际冲突”;而最后那些企鹅、油桶及在巨浪前哀嚎的儿童则显然指向决定人类未来生存状态的“环境危机”。可以说,《黑雨系列》是通过“传统中国”、“革命中国”、“改革中国”、“国际冲突”、“环境危机”五个主题对二十世纪至今的中国和世界展开反思,画家的立足点是中国,但所展望的却是人类整体。因此,《黑雨系列》尽管只有少数几幅有明确的历史事件,但却是底色十足的历史画。我之所以这样断言,除了上文分析的理由外,更主要的理由仍然是这些作品中所蕴含的历史意识(而不仅仅是有关历史的符号)。在我看来,贯穿这些作品的历史意识仍然是典型的批判式的。上文所引尼采的话,已经指出批判式的历史意识与主体的痛苦和被解救的欲望有关。可以说这也正是谭根雄许多作品共同的主题。红色革命和脱衣舞女究竟带给我们什么?那些困在黑色和灰色中的婴儿将会有什么样的未来?让人触目惊心的战争混乱和环境危机是否就是人类必然的归宿?凡此种种都是《黑雨系列》引发观众思考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无不指涉一种客观存在的生存的痛苦。由于意在引起反思,所以《黑雨系列》的历史意识实际上和非常规的配色及线条运用共同构成批判的手段。
黑雨系列 120cmx150cm 布面油画 2009
黑雨系列 180cmx200cm 布面油画 2011
二、以人的价值超越政治
尽管有许多敏感的批评家力求描述当代艺术的演变轨迹,通过年代区分的方式观察 80 年代、90 年代、新世纪中国艺术的不同阶段性特征——这种努力值得肯定,因为作为历史的在场者我们总需要为后来者提供一些关于历史书写的参考意见。但我们还是必须清晰地意识到,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应该过度强调每个阶段之间的差别。就新时期来看,这三十多年的艺术状况在形式多变的外表下仍有其统一性。无论如何,把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张力视为这一时期中国文艺(这里所指的主要是通常所谓的“纯文学”和“前卫艺术”)艺术意志的来源应该说并不算太离谱。换言之,政治始终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核心话题。
如果要描述这一时期艺术精神发展的话,我们可以将在与国家意识形态对抗过程中个人主义的日益扩张视为一条主线。这在文学和艺术中均有相似的表现。高名潞总结中国当代艺术精神的发展说:“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的二三十年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始终在寻求个人价值,但不同时期的着眼点不同:20 世纪 70 年代末是‘人道’,是关于一个人存在的道理;80 年代是‘人本’,是关于一个人存在的本质问题;而90 年代则是‘人态’,是关于一个人存在的状态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个人主义是不断扩张的,就是说个人意识越来越强烈。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当代艺术中的个人意识始终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反面存在的,追问的是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个人能够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
新凯恩斯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 B 240cmx180cm 布面油画 2010
从早期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到《紫禁城系列》,我们可以看到谭根雄作品中个人意识的发展。《紫禁城系列》的抽象画法,解构了皇城的崇高物质形象,以混沌模糊的样式呈现象征政治权力的皇城。这样的艺术手法本身即拥有一种与权力对抗的力量,一如波洛克以其连续不断的繁复线条确证了艺术行为的在场。《紫禁城系列》的个人主义体现在以纯粹自我的视角对政治进行居高临下的审视。
《黑雨系列》中关于政治的批判与关于人的价值的追问,和《紫禁城系列》相比又不太一样。这些作品批判的对象不仅仅只是政治意识形态中权力对个人的压抑,同时也包括消费意识形态中商品对个人的异化。换言之,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在画家的反思与批判之列。而画家反思与批判的立足点和最终指向则是人本身的价值。
黑雨系列#105 150cmx120cm 布面油画 2012
让我们从主题最明显的《黑雨之柏林墙》(一、二)说起。从策展的角度说,两幅《柏林墙》具有分章节的功能,但这个功能是建立在作品自身的意义之上的。两幅《柏林墙》可以说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同一堵墙,但也可以说是以同样的技法表现墙之两面。众所周知 , 柏林墙自 1989 年柏林墙开放之后,原先用以隔绝东西德的交往,象征着意识形态对峙的墙体就成为众多艺术家涂鸦的巨幅画布。谭根雄这两幅作品的创作灵感无疑来自如今涂鸦遍布的墙体。让我感兴趣的是,这两幅作品到底哪一幅指涉东德,哪一幅指涉西德?看起来,灰暗沉闷的第一幅指涉的应是东德,而鲜红艳丽的第二幅指涉的应是西德。画家在第一幅的整体灰暗中添加了一些红色的元素,而在第二幅整体的鲜红中又添加了一些灰暗的元素,两幅画构成严格的对立又互涉的关系。画家似乎意在传达东西德的意识形态虽截然对立,但意识形态的对立并不能彻底消灭人性中某些共通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出画家的立场既不在于东德,也不在于西德;毕竟灰暗沉闷表现出明显的压抑感,而鲜红艳丽也暗示了某种颓靡感。我想,与这种压抑感和颓靡感一并对立的人自身的价值才是画家真正的立场所在。
当谭根雄的画笔回到对中国事物的表现时,这种立场显得更加明显、大胆而有力。在这些作品中,象征政治的元素极为刺目。在构图上,或者以后景的方式呈现(如国旗),或者以前景的方式呈现(如雷锋头像),这些政治符号总是能够迅速地吸引观众的目光;但无论以何种方式呈现,这些符号似乎总是在承担装饰的功能,似乎永远无法成为画中人物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在面对这些作品时,观看者总会下意识地将这些符号与人物剥离开来,并且意识到二者之间的对立。有意思的是,画家同时将象征革命意识形态的雷锋头像和象征商业意识形态的迈克尔·杰克逊的头像同时画在婴儿襁褓的裆部。这样的生硬、突兀的处理方式,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其意义不言而喻:无论是政治还是商业,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是本土的还是西方的,在人本身的价值面前,都只是一个可笑的装饰而已。
毫无疑问,人的生命和存在是《黑雨系列》关注的核心。然而,画家所宣扬的人的价值并非单纯的个人主义。一如上文所指出的,对国际冲突和环境危机的关注,使画布上的“人”从个人延伸到人类。这充分体现出谭根雄身上还保留着浓厚的“八十年代”气质,我所指的正是对宏大主题的关注及对启蒙理性的坚守。这使得谭根雄能够与当前艺术潮流中因不断膨胀的个人主义而导致的虚无感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不是说谭根雄的作品中没有虚无感,事实上,《紫禁城系列》和《黑雨系列》都有相当浓厚的虚无感;重要的是在虚无感的背后画家仍在以有力的笔触叩问艺术的使命和人类的存在状态及未来的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黑雨系列》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当前中国艺术热衷于以个人主义非理性地对抗意识形态的冲动。
紫禁城1号 100cmx80cm 综合材料 2005
紫禁城18号 120cmx100cm 综合材料 2008
三、通向一种交互主体式的表现主义
力主表现论的艺术理论家科林伍德曾断言:“艺术必然是语言。”艺术作品的语言,或构成一件作品的所有形式因素,必定与艺术家言说或观看的立足点息息相关。作为一种美学主张的表现主义原本是针对模仿 - 再现的艺术观念而提出的,尽管其核心理念在于情感表现,但表现何种情感、何种对象的情感及以何种方式认识情感却导致表现主义倾向的作品呈现出极其多元的特征。为此,我们使用表现主义这样的词来指称当代艺术作品需要保持谨慎。
上文已经指出谭根雄作品在手法方面的复杂性,因此我无意为谭根雄贴上表现主义的标签。但《黑雨系列》最杰出的部分无疑是以婴儿为主体的那几幅带有浓厚表现主义倾向的作品,尽管以超现实主义手法表现战争想象的那几幅在视觉上更具冲击力,更能够在瞬间紧紧抓住观看者的注意力,可是却不如那几幅表现主义倾向的作品耐人寻味引人深思。现在我想针对这几幅作品分析《黑雨系列》的表现主义特征。
材料108号 240x360cm 印刷铝板、油漆、指甲油、聚酯 2015
艺术史上的表现主义风格从一开始就与抽象紧密相连,这是表现主义者力图将事物的形式转变为某些特殊感情的载体的必然结果。这些感情最常见的无过于艺术家个人的激情。《紫禁城系列》正是属于这一类作品。在那些作品中,画家将自我的感情直接倾注于混沌的色彩和粗砺的线条中,因此彰显出表现主义艺术一贯的热烈、狂躁和不安的特征。彭锋曾指出:“谭根雄的抽象绘画,就是这种在混沌与有序之间寻求平衡的艺术。谭根雄不仅将波洛克式的混沌与蒙德里安式的秩序调和起来,让它们处于互相制约、冲突、激发与和解的动态平衡之中,而且将具象与抽象调和起来,创作了一批半具象半抽象式样的绘画。”波洛克式与蒙德里安式的调和用来描述《紫禁城系列》很是准确,而具象与抽象的调和似乎更适合于描述《黑雨系列》。
《黑雨系列》的主体大多以具象的方式呈现,而背景则多以抽象的方式呈现。我们看到画布上婴儿的身体和表情几乎全部都遵循严谨的写实技法,而背景则一片模糊,或许我们可以直接说这些画是没有背景的;画家将那些婴儿画得那样硕大突出,几乎占据了整个平面,以至于不得不取消画面的纵深,代之以混沌模糊的灰暗。这当然是一种抽象。具象与抽象的结合使得这些作品产生出某种奇异的效果:我们看清楚了一些东西,但看不清楚另一些东西,确认与疑惑这两种矛盾的感受在我们心中交织着出现。某些时刻,我们觉得那些明晰的主体将被模糊的背景吞没;某些时刻,我们又会觉得这些主体似乎正从背景中浮现出来。
与这种奇异的审美效果相关联的是,在具象与抽象的形式之间,作品中所表现的情感似乎也获得某种平衡。当观众凝视着画布上那些婴儿或熟睡或哭泣或惊奇或打哈欠的神态时,可以自然地体会到两种感情:一种感情是由具象的婴儿(儿童)激发起来的。他们看到什么意识到什么或者梦到什么,因为什么样的感受,于是有了这样的神态?对他们,我们很想知道点什么,比如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是否和我们有着同样的体验世界的能力?另一种感情则来源于画家的表现方式。画家为何将刚刚来到世上的他们画成灰暗的,为何将他们置于一片混沌的灰暗底色之上,画家对他们怀有什么样的感情?两种感情激发机制互相牵制平衡,使得《黑雨系列》的大部分作品在情感表现上呈现出一种相对内敛克制的状态。这与通常的表现主义绘画情感张扬的气质颇不一样。不过在我看来,这也正是《黑雨系列》在美学上最重要的成就。
纸鸢 120cm×140cm 布面油画1985
狗男狗女 80x96.5cm 布面油画 1979
我将《黑雨系列》的这种情感表现方式称为“交互主体式的表现主义”,所指的正是这些作品所表现的不仅只是画家的感情,更是在画家与模特之间形成的交互主体的感情。据画家在展览会开幕式上的介绍,画中婴儿主要是以自己的女儿为模特。明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对这些作品中的交互主体做出更加充分的阐释。在我看来,画家并不是把模特作为一个物化的对象来表现;他对模特(女儿)怀有一种深厚而复杂的感情,他携带着自身对世界的体验却借用模特的知觉来感受。也就是说作品所表现的情感实际上是画家意识中自我的经验和想象中模特的经验的融合而产生的。于是我们感受到悲观(灰暗的色调),来自画家自身的经验,感受到不安(婴儿的眼神、哭泣和其他表情),大概来自画家借助模特幼小的心灵来感受世界,感受到希望(红色的苹果)。大概来自画家对女儿的期许。总的说来,就构图和色彩的运用而言,《黑雨系列》比画家之前的作品都要简单,但所表现感情的复杂程度却远远超过之前的作品。而且这些感情已经加进去非常浓厚的理性思考的成分。比起《紫禁城系列》局部所呈现出的非理性的张狂,《黑雨系列》显得更加有序。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当我面对这些作品时会产生出“谭根雄又变了”的感受。
或许有人要问,这种更加内敛、理性、有序的情感表现方式,在多大程度上还符合表现主义的美学特征?的确,典型的表现主义风格体现为情绪情感在媒介上的直接表达,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但表现主义在历史上向来是极其多样的,富于发展的,从来不是铁板一块。蒙克说:“我要描绘的是触动我心灵的眼睛的线条和色彩。我不是画我所见到的东西,而是画我所经历的东西。”如果说这一主张足以为个人(个体)式的表现主义立法的话,那么,如果我们转而去画我们意识中他人所经历的东西,就很有可能导向一种“交互主体式的表现主义”。在这种表现方式中,艺术家个人的感情保留了下来,同时又因与自身之外的人或物保持了联系,因此变得更加清醒、谦卑。表现主义的末流往往情感重于形式,以至于在艺术上常招来粗糙之讥,而注重主体间对话交流的情感表现方式似乎有助于克服这一流弊,这一点只要想想布莱希特对表现主义戏剧的改进即可理解。我想,《黑雨系列》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尝试和探索。
( 薛学材: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
禁止做人(五联画) 150cmx600cm 布面油画 2009
柏林墙(三联画) 200cmx480cm 布面油画 2008 (请横过来观看)
六十人生埠岸
文 _ 谭根雄
稍加留意,20 世纪 50 年代出生的人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开放年代,他们所理解的当下社会根植于凯恩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土壤,囿于此,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成了这一代中国人的艰巨理想构筑。今天,用调侃之辞形容这一代人要抓住还在沉重喘息的生命,且在离去人生不远的埠岸上迸发自己最后耀眼的“剩余价值”。
是的,蓦然回首 60 年的风风火火:我们曾是铁杵淬火锻造的一代,或“折腾”的一代,也是受尽白眼、饱尝劳累、精神趋于疲软又即将被后来年轻者颠覆的一代,或是前半辈子命运多舛、道路坎坷、荒废青春作为的一代,但是,那远去的沸腾热血的蹉跎岁月,它毕竟成了这一代人最为鲜活的集体记忆。
20 世纪 50 年代,我出生于上海四川北路。这是一条商业大街,在英制轨道电车驶过的马路两边,各种幡号的店肆小铺一家挨着一家,空气中弥漫着兜售生意的吆喝,其声音此起彼伏,南腔北调混杂着一派特有的海派韵味,无论是白天还是掌灯的傍晚,一年四季人流不息,终日喧嚣着行人来去匆忙的焯焯影像;无疑,它为上海滩市井生活勾勒出一幕幕热辣的世俗盛景。尤其在夏天半夜,倾听木棂长窗外的东南风阵阵送来黄浦江上轮船低鸣汽笛,其分明辨析那悠远又混杂着忽近或远遁的岁月沧桑之感。顿时,我怡然于一派无限的想象,在清晰与缥缈的时空中而松懈懒慵的身心,渐渐远遁。
那时,我家油漆斑驳的老宅大门上贴着一副墨迹已褪的“跟共产党走、听毛泽东话”的对联。其遒劲的正楷字体在被衬映于历经岁月洗刷得泛白的红纸上显得更加赫然明目,它成了我的童年、少年,乃至前半生的、唯一触动灵魂的视觉印记。如今人们不必再去遑论各种社会运动,我们诚然是摇滚大腕崔健所唱“红旗下的蛋”,孵化出了我们一生幸福,即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城里人照旧吃得饱、穿得暖。“我们活得蛮好的”父亲经常敲木鱼似地对我说。
20 世纪 50 年代出生的人,如今,他们身心的真正成长和业绩所长之日正逢上“改革开放”好日子的到来,尤其是绘画界顺应时代剧变而发展到了振聋发聩的地步,尽管,我预设自己虽老有所学却不及前辈,创新思维又恐怕落伍后生,这种个人内心纠缠的矛盾,是自知之明的。过去的思想禁锢,包括陈旧的艺术形态业已不足再秉承社会发展风气,换言之,我们这一代虽然顾及“潮流”风骚,愿意心胸开放,接纳新生事物,但因缘自身学养缺失或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其结果是可以预料的。正因如此,我的思想无法从根本上升腾,也无法让自己真正的脱胎换骨。用“捉襟见肘”的尴尬来比喻 50 年代出生的人,是最为恰当的解释,我们艺术气息比平庸的脂粉美人稍微好闻些罢了。在这里,我完全可以毫无顾忌地说 50 年代出生的艺术家其实不算什么。因为,我们即将面对死亡与腐化结合在一起的来日并不太远;也因为中国现实中的复杂性与演化性的实践观察,让我十分明白了本文开头叙述祖上老宅木门上的对联内涵。报刊、文章上经常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成了我们走向地球东半部地平线上的人类前行的光明通衢。
无疑,50 年代出生的艺术家崇尚生存哲学,并不长期纠缠于艺术中的指涉问题,尤其在现今的文化语境中,艺术已经不再是技术上的任何表现或指代学术道德等人文态度,抑或是社会责任和立场等斩断了历史的情缘之后,正在支付的却是意义和价值真空的代价。尽管我们所创造的那些“作品”曾经是多么地真实,多么为人挚爱,且“指物造境”甚至“唬人噱头”,不啻是吹毛求疵或委曲求全。但问题是我们如今仍然有着这么一种心态:与我们曾经历过的岁月保持嗟商对话的诚恳愿望,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投射了我们已是眼下的“既得利益者”形象。这不是虚幻,是实实在在未被虚饰的自我真实生活。至少,我们可以用画来养活自己。这正如在1931年胡适《四十自述》中描写梁启超“换了方向走了”。在这个时候,我不免感觉一点失望。但这种失望也正是来自于当今“知识分子”的良心发现。因为是“良心”力竭所能,如同养儿育女一般,它把人生的希望带到了一个崭新的生存境界,漂泊于一个更为透澈碧清的六十人生埠岸。
SOS—X波段1号 110x90cmx3 布面油画 2018
谭根雄版面效果
合作或投稿
请发邮件至:maanart@163.com
或致电:010-80780866
本周热门
更多- 01 陈文骥:边缘化是我的生存习惯
- 02 谭平 : 从空间里长出来的绘画
- 03 徐冰:艺术从来不是一个时代的光亮
- 04 尹朝阳 : 真正的困境在圆熟之后
- 05 徐累: 普适的内观
- 06 丁立人:我画《西游记》
- 07 沈勤:放逐的诗意
- 08 武艺:内观与旷达
- 09 岳敏君:持续虚无
- 10 尚扬 : 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