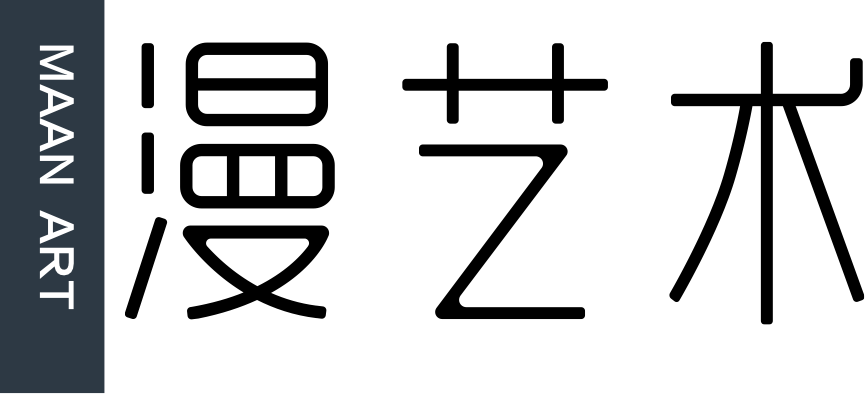高炀:艺术即信仰
搜索公众号「漫艺术」可快速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漫艺术》杂志2018年5月新刊
1965年出生于中国内蒙古,1997年加入意大利国籍,现生活创作于中国北京。
1989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199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六届研修班,毕业创作《沙麦女人》获全国油画艺委会优秀作品奖,其后入住北京东村,开始背离学院派艺术,创作了第一次个展的30余幅以综合材料表现主义题材的作品,并于东村张洹等人共同创作了行为艺术“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九个洞”,参加了第四十八届威尼斯双年展,这些作品引起了国际艺术届的关注;
1997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作品有“状态”与“肢解”系列。同年赴意大利工作并定居于欧洲文化艺术中心城市米兰与都灵;1999年参加意大利都灵市“国际大都灵”双年展的外围展;2000年参加了欧洲艺术联盟举办的“arte al muro”展等。代表作品有大型综合材料系列《印象》及《圣婴》;2001年在意大利当代艺术基地举办个展及行为装置艺术《黄帝与欧罗巴的对白》《权充者》;2003年在北京798举办个展及三人联展;2005年至今生活工作于北京,并参加了广卅三年展和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展;回国几年来创作了大量作品并形成个人风格得到艺术届的关注与好评,其代表作为《迷失的头像》《城市日记》《印象》《状态》《公共洗衣机》《界》《综合材料》等。作品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主要题材。以独特的个人视角反映了当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及人的生存状态,反规则性与反继承性是这些作品的突出特点与表现形式。
2005-2015年,《时间的日记》,欧洲六国巡回展。2015年7月在威尼斯举办高炀个展。
发言人系列 2 60cm×70cm 综合材料 2017
高炀:艺术即信仰
采访 _ 胡少杰
漫艺术= M: 您是中国最重要的行为艺术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也因此早早地进入了艺术史,后来也陆续创作了一些行为作品,但是您主要的艺术脉络还是架上绘画,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高炀= G: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去年肖鲁也问过我类似的问题。其实是这样,当年的东村确实是充满了一种乌托邦式的、虚无主义的气息,大部分住在东村的艺术家都把注意力放在了用身体、用行为来表达这种集体的、荒诞的艺术思想,整个东村都是这样一种氛围,而且也做了一些非常有话题性的行为艺术作品。像我参与的《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九个洞》等,引起了完全超出我们想象的巨大反响,但是我始终认为这种艺术表达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它很快就会过去,所以在当时我也一直在坚持架上绘画和装置艺术。这种对艺术相对冷静的思考也让我和东村的其他艺术家形成了一种隔阂。我没有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行为艺术上面,而恰恰选择了坚持我个人的一种艺术方式。我始终认为个体性是一个艺术家必须要坚守的,这是和东村其他艺术家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当然我们在生活上、艺术上也保持着正常的交流,只是对艺术的认识上有一定的分歧。但是不可否认在东村的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艺术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无名山增高一米》这件作品也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声誉,以至于我去欧洲求学和生活时,也会被不断提起,成了一时难以揭掉的标签。
发言人系列 1 60cm×80cm 综合材料 2017
M: 您 90 年代末到欧洲,到意大利,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您怎么处理自身的身份属性和所处西方语境之间的关系?
G: 这是一个困扰了我很长时间的问题。刚去意大利的时候经常会被误认为是日本人、韩国人,没有人会认为我是中国人。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中国人不应该是我这个样子,他们对中国人的印象还停留在留辫子的清朝时期,或者是改革开放前,他们认为中国只喝茶,不喝咖啡;只吃饺子,不吃三明治。这种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隔阂非常严重。他们把这种民族身份固有的、概念化的印章印在中国人的脸上,这让我很困扰,很不舒服。所以后来我开始用艺术的方式来对抗他们的这些固有观念,反对他们的概念,用艺术的方式让自己成为一个解码文化偏见的发言人。
综合材料 1 60cm×70cm 综合材料 2017
综合材料 2 70cm×80cm 综合材料 2017
M: 用西方式的艺术语言,表达中国人的当代思考?
G: 我必须要用西方的模式,必须要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艺术缺乏一种国际语言,你必须要承认,当代主流的艺术语言是在沿着西方的艺术史脉络一直发展形成的,你不能拿着一个毛笔、背着一个墨盒去和西方人较量,这太荒诞,完全是“孔乙己”。所以必须承认我的艺术语言首先是受了西方艺术教育的一个结果,从文艺复兴到现代派,一直到以美国为中心的当代艺术,我必须要强调这个脉络,如果把这个否定掉,我的创作也就无意义了。我的作品中体现的符号学、文化学、人类学、生物学等种种西方多元的文化概念,就无所依附了。
综合材料 4 50cm×70cm 综合材料 2017
综合材料 3 60cm×80cm 综合材料 2017
综合材料 5 80cm×80cm 综合材料 2017
M: 意大利作为西方艺术的源头,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现当代艺术也是大师辈出。在这里长期地求学、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G: 90 年代初期,经过 10 年的改革开放,在国内已经基本上可以大致地了解到西方当代艺术的基本情况,所以对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这些西方主要的艺术策源地非常向往。后来我有幸到意大利去读书,去了之后发现这个国家无论是古典艺术还是现当代艺术真的极其丰富,处处充满了艺术的气息。他们的政府包括平民甚至把艺术作为一种和世界较量的重要筹码,他们很大程度上的国家自信都来自艺术行业的发达。他们特别注重和鼓励当代艺术的发展,鼓励年轻人去从事像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等种种前卫艺术,然后跟进严谨的学术研究,他们要和德国人较量,和美国人较量。另外他们对外来文化也特别感兴趣,对非发达国家的艺术也在积极地研究,整个国家呈现出的是一个既厚重又开放、多元、包容的状态。我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学习和工作了十年,这对我的艺术影响非常大,包括我对艺术的认知,对艺术价值的判断,包括艺术语言的选择,都是在这时期逐步确定下来的。
M: 应该是 2008 年左右,您的作品开始大面积地转换成现成品综合材料,这次变化背后的契机是什么呢?
G: 材料绘画其实很早就开始了,从东村开始接触的材料艺术,1993 年中央美术学院画廊个展,范迪安参加开幕式并给出了好的评论,只是在刚回国的那几年,有过一段单纯的绘画时期。主要是因为我回国后发现中国的情况特别复杂,也很混乱,我需要一个时期来适应它,需要一个冷静和调整的阶段,所以就画了两年单纯的油画。后来我发现处在中国这样一个艺术泡沫的时期,无论什么样的艺术都没人去认真严谨地对待。经过几年的适应和调整,我又重新恢复了材料绘画和装置艺术的创作,重新找到了应对中国现实的表达方法。从这之后开始大面积的创作材料作品,在语言上看似是西方贫穷艺术的方式,但是对应的却是中国本土性的文化现实和社会现实。
M: 但是艺术语言背后的逻辑,还是承袭了贫穷艺术?
G: 有类似的地方,但是并不是完全相同,因为贫穷艺术有明确的定义和范畴,我的艺术在材料运用和作品的气质上可能一定程度上承袭了意大利贫穷艺术,包括对消费主义的消解和反抗,这同样是当下的中国所需要面对的问题。当时意大利反对的是以美国为主的流行文化,当下的中国面对西方的文化殖民也依然需要有自己的态度,要坚持本土性,否则就会逐渐被同化,最后整个文明都会被毁掉。
M: 前面提到,您并不讳言您的艺术语言以及您对艺术的认知是西方式的、国际化的,那么这种国际化和您身上自带的本土性的文化基因、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您怎么处理?
G: 我回到中国以后,慢慢发现确实要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也是近几年工作的重点。贫穷艺术这个帽子戴得越久,我越觉得必须要摘掉它。因为我的潜意识一直不停地提醒我,你是一个东方人,而且你是一个当代的中国人,你的文化身份跟他们完全不一样,你脚下的土地才是你的根基,你可以运用国际化的语言,但是你必须找到你的本体文化,找到你自身的社会现实,这样你才能真正创作出真正独特的艺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艺术。现在意大利的艺术家看到我的作品,他们认为越来越不像贫穷艺术,这就是我的目的。其实艺术家创作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是寻找自我的过程,当年我为了寻找它去了欧洲,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然后发现这里才是真正的归属之地。这是一个艰苦的蜕变的过程,用了我大半辈子的时间。
综合材料系列 3-1 60cm×90cm 综合材料 2017
综合材料系列 3-2 60cm×90cm 综合材料 2017
M: 强调本土性是您未来艺术的一个长期计划?
G: 我觉得这值得长期来做,我多年的经验告诉我,这必定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工作。而且我确实要制定计划,包括创作和展览。我觉得有必要让西方的艺术界看到什么是不一样的当代艺术,让他们感到有威胁,打破今天西方式的艺术体系。这看起来有些狂妄,中国文化一直都太含蓄了,在今天这个时代需要直接一些、强势一些,需要激情和理想主义。艺术需要理想主义,艺术家更需要理想主义,否则就很难爆发出创造力。因为艺术不是科学,艺术的最大价值是创造,如果对艺术没有激情和理想,那你和一个铁匠或者油漆工没有什么区别。
M: 这种理想主义,这种激情化的创造力,其实是对自身的一个消耗。所以一般伟大的艺术家都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G: 艺术家不能带着功利之心去权衡这些问题。因为既然选择了艺术,就要把艺术当成至上的理想,其他的很难再去兼顾。我自身因为艺术放弃了太多东西,婚姻、家庭、社会地位等,大半生都献给了艺术,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我认为非常值得,因为艺术给了我比世俗生活更大的价值感,也给了我快乐。
M: 您平时怎么保持您艺术创造力的持续性呢?因为您好像更多的时候是依赖激情化的,不确定的类似于禀赋的东西。
G: 当然不能完全靠感性支撑,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大量地阅读和思考。因为艺术需要激情,也需要思辨的判断,这些必须依靠理性思维。我平时的阅读量很大,涵盖东西方各个领域,我懂三门外语,自修了英文、日文、意大利文,所以在阅读上一般没有障碍。长期的阅读和观看给我提供了思辨能力和逻辑能力。这些都有助于我的艺术创作。
综合材料系列 2-1 60cm×80cm 综合材料 2017
综合材料系列 2-2 60cm×80cm 综合材料 2017
M: 这些阅读积累的知识经验对您个人性格中这种原始的创造力是否会有一定的消解?
G: 这需要你来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平衡能力需要长期训练。我对艺术的判断,首先是靠我的本能、我的个人情感,然后会下意识地调动理性的知识经验来辅助判断,但是却不能完全依赖于知识结构,最终要从里面跳出来。这种平衡能力其实决定了一个艺术家的高度,因为它关乎于这个艺术家的禀赋才情和后期知识的建构,这在作品中一定能够体现出来。
M: 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从事艺术行业近三十年,这个过程中对艺术产生过怀疑吗?对自己付出半生的事业,怀疑过吗?
G: 之前确实怀疑过,但很快打消了。我不是一个聪明人,不像杜尚那样,可以说否定就否定,说放下就放下,我做不到。我把一切都献给了艺术,我发现我已经没有怀疑的余地了。所以后来我就孤注一掷,就算这样看起来并不聪明,甚至很笨、很傻,我也绝不怀疑。我不怕失败,不怕被别人否定,就算所有的人都认为我这是死路一条,我也绝不后悔。我会一直笃信艺术,笃信自己。
M: 您这是一种殉道精神。
G: 既然选择了艺术,就要把它当成信仰。高炀的艺术是不可复制的。
综合材料系列 2-3 60cm×80cm 综合材料 2017
从艺术家本身的生活方式理解这种非定义性的当代架上艺术,不难看出画家对“人”与“物”关系的理解已经超出了流派的局限。20 世纪 70 年代的“日本物派”到“八五新潮”革新式的创造,艺术家们在不断尝试融入本土性的文化意识,从而创造出普世性的语言,来减轻同化带来的危机感。对同样身处这个时代的艺术家来说,选择西方求学并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想是有风险的,但高炀在身处意大利这个近乎西方艺术发源地的环境中依然坚持融合本土意识与西方审美实验。这在当时也许并没有过多的目的性,但是据艺术家后来自述时回顾,那是一种很自然的自我认同感。同时,深受意大利贫穷艺术主义与综合材料影响的他,之后依然承袭了其中的元素却并没有一直禁锢在流派限制中,尤其在回国后,观察并研究中国当代社会文化与传统中国绘画特点。高炀通过 10 年对西方审美的沉淀式理解与尝试,加以本身与后天的中国社会经验,最终创造出了一种带有和谐感的绘画理解。
而从本次作品“发言人系列”来看,画面表达虽然承袭了画家个性化的社会含义提取,却又重新调整了元素的搭配,加入了头像这个易与观众沟通的关系。从另外两幅较早期作品中直接的材料表达,《发言人》似乎选择了更为整体的意识传递,减弱了物性的突兀和分隔感。相比于其中两幅较早期的作品,艺术家的意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主观的情绪感染,使得其从表现主义的基础上融入了客观的审美理解。艺术家通过快递包装提取出当代市井文化中的快节奏,意指群众因及时快感的麻木而导致被真正美学抛弃的批判表达。另一方面,作品中大篇幅的颜色对比并没有失去系列之间的连接感,这种细腻的处理并不是带有目的性的交流,而是对自身情绪的客观表达。综合材料的选择和色彩的搭配使画面表达更为和谐和沉稳。
这个时期的高炀对材料的理解已然过渡到对语言的处理,这种语言不仅是画面的整体性,而且是一种自省式的内心表达,色块与材料的对比始终在互相呼应互相表达艺术家的意识。从看似带有构成主义的构图中又能找到中国艺术家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又能通过油画笔触及材料的纹理极其自然地融会贯通地增加作品的力度感。不同于装置艺术、新媒体艺术,高炀的综合材料绘画所特有的学术价值与信息量是巨大的。因此在不断进行实验性的绘画尝试与自我审视后,表现出的就是这种带有普世性的绘画语言和非定义化的审美体验。
——高嘉浦
| 高炀版面效果 |
合作或投稿
请发邮件至:maanart@163.com
或致电:010-80780866
本周热门
更多- 01 陈文骥:边缘化是我的生存习惯
- 02 谭平 : 从空间里长出来的绘画
- 03 徐冰:艺术从来不是一个时代的光亮
- 04 尹朝阳 : 真正的困境在圆熟之后
- 05 徐累: 普适的内观
- 06 丁立人:我画《西游记》
- 07 沈勤:放逐的诗意
- 08 武艺:内观与旷达
- 09 岳敏君:持续虚无
- 10 尚扬 : 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