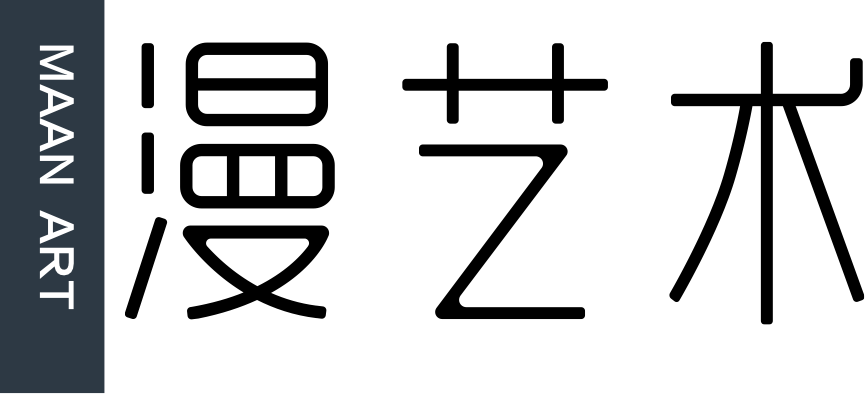《在场者的荣光:1979-2019中国当代艺术四十年个案样本》,由漫艺术机构与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联合出版
 访谈内文
访谈内文

|批评家访谈|
杜曦云:当代艺术是当代文明的艺术表达
采访 _ 胡少杰
漫艺术=M:大家通常把1979年这样一个历史节点,看作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元年,您认可这种带有断代性质的划分吗?
杜曦云=D:谈“当代艺术”的起点首先要廓清什么是当代艺术。我认为当代艺术是当代文明的艺术表达,用艺术的、美学的方式来表达当代文明。当代文明的核心动力是在求真的基础上求自由,由此发展出文化上的个人主义,经济上的自由市场等。这样的话,我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明确起点是1979年下半年的“星星美展”。
“星星美展”的作品一出场就打动那么多人,和以前的红光亮、高大全的作品相比,“星星画会”用艺术的方式说出了他们的真心话。一群根本不在册的野生、业余艺术家,在中国美术馆旁边的栅栏上挂的作品,居然一下就让很多市民特别喜欢。包括第二届“星星美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破了记录,参观人数超过10万人,平均每天有6000人之多,排队的队伍就有几百米长,可见被认可的程度。
 第二届星星美展观众排队场面
第二届星星美展观众排队场面
他们的展览方式也很符合当代艺术拓展自由的气质:殿堂级的官方美术馆不让我展示,我就在旁边的栅栏上挂出来……包括展览被查封后的维权行动。从作品本身和作品展示的方式等各个方面来看,它都非常符合当代艺术的定义,而且他们一出场时就这么准确、清晰、坚定,简直就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标准样板,到现在为止我觉得都没被超越,把“星星美展”称为中国当代艺术的起点,我觉得实至名归。
在“星星美展”前后,北京、上海、重庆等地就有类似的艺术活动,出现了一些不以官方主流艺术的方式来创作的个体和群体,这都很可贵。但是他们的清晰、勇敢的程度,包括作品本身的展示方式,以及延伸出的意义等方面,我觉得和“星星美展”相比是稍逊的。
M:因为时代背景不同,所以之后的艺术家不再具有当时的历史语境,所以很难超越?
D:不仅是这个原因。今天的艺术家也依然需要直面很多问题,但他们做了什么了?当年“星星画会”的作品,用各自的方式表达他们看到的事实和心里的真话,反过来再看如今的当代艺术作品,我们不妨问问自己:感动你的有哪几个人、哪几件作品?
我觉得“星星美展”的这些艺术家,头脑很清醒,意志很坚定,而且富有行动魄力。反倒是今天很多号称是当代艺术家的人,打着当代艺术的幌子,真正搞懂当代艺术并去践行的人没有多少。
M:那么这40年时间,包括当时那批人现在依然在创作,这40年他们的工作价值如何评定?
D:我认为这40年里面,很多打着当代艺术旗号的人做的根本不是当代艺术,或者虚有其表。“星星画会”了不起的是:直到现在为止,在中国当代艺术界,获得了国际声誉的、能量最大的、最有魅力的基本上还是一些当年“星星美展”的参加者。
艾未未《葵花籽》
M:您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呢?除了历史价值之外?
D:我觉得艺术的评价标准不外乎是智慧和美感。智慧主要是谈作品的内容,矫情一点叫作“所指”,再矫情一点叫作“观念”。美感的话,过去叫形式,矫情一点叫作“能指”,再矫情一点叫“语言”。如果在美感方面有所创造,但基本立场和智慧含量稀缺的话,这种作品就有大是大非方面的问题。比如希特勒的御用导演莱妮·瑞芬斯塔尔,在美学方面有大的创造,但表达的是纳粹思想。作家毛尖评价她的作品:非常美,非常罪。
莱妮·瑞芬斯塔尔与希特勒
M:那在您看来,当年星星画会的那批艺术家,是否符合您这两方面的标准?
D:我觉得当年的很多艺术家在语言方面显然是不成熟的,比如有些人明显是东拼西凑地借鉴现代主义的样式。但最起码他们已经在追求现代主义的多元和开放了。而且,其中也有少数人在当时就有一种本能的原创,艺术水准很高,没必要妄自菲薄。
M:您关注和评判一个艺术家主要是看创造力,还是看他语言的成熟度以及持续性?
D:这很复杂,但艺术家主要还是靠作品说话。艺术属于创造,有些时候是说不清楚的。一个人勤学苦练几十年,但临门一脚时就是踢不进去。另一个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一刻上帝眷顾了他,那一脚就踢进去了。如果某个作品打动了观众,观众会在认可作品后,回过头来看艺术家平时的表现。
M:作为一个批评家和策展人,在建立了自己的评价标准或者话语系统之后,是否也意味着在建立一种话语权?个人的话语权一旦建立,怎么来规避个人偏见?怎么去保持客观?
D:最重要的是无限接近真相本身,有没有话语权应该是第二位的。
M:事实等同于经过时间的考验最终留下来的所谓的美术史吗?
D:我觉得“经过时间的考验最终留下来的”这句话忽视了当下的时效性。历史在不断生长和流变,杜尚就说过:艺术史每30年一变。最重要的还是活在当下的你觉得它到底是不是有价值,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M:如果不以时间为终极的评定标准的话,那它的终极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在您看来?
D:我觉得艺术的价值始终在于此时、此地、此人。每个人对艺术作品的看法都不一样,而且同一个人在不同情境中的看法也在变化。面对变动不休的水流,难以抽刀断水,刻舟求剑。
M:会存在一个基本的共识吗?
D:你认为是否存在一种普遍的人性?
M:普遍的人性?我觉得应该是存在的。
D:那这个基本共识其实就是普遍的人性,在这个基础之上产生的普适价值。
M:普遍人性,普适价值,是恒定的?还是随着时间在变化?
D:它是开放的。但另一方面,从古至今,人性本身没有变过,那些欲望、意志、需求。
M:那艺术需要面对和印证这种普遍的人性吗?
D: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做出来的东西,不同的艺术家做作品时的目的不一样。
M:您怎么看待如今不断更新的新媒介、新科技对艺术发展所起的作用?媒介的滞后或先进和艺术本身的价值存在必然关系吗?
D:人类的生存处境每一刻都在变化,但人性没有变过。艺术史的大变革往往是因为:一方面,艺术内部发展到了大家渴求发生大变革的时候;另一方面就是外部因素的冲击或启发,比如新科技的出现。
今天的新媒介已经不是声光电,是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这种前所未有的更发达的技术,一定会给艺术带来大变。但另一方面,人性本身又没有变过。这二者之间会形成一种张力关系,不变的依然不变,能变的会发生大变。
M:作为一个青年评论家,您对美术史的书写有兴趣吗?您觉得这是作为一个研究者必要的责任吗?或者这似乎也是一种建立话语权的有效途径?
D:以往我没有这个冲动,现在我想选择一些我认为最有意思的个体,写一系列深入的个案。艺术是创造,有很多东西难以说清楚,艺术史的星空归根到底是由一个个杰出艺术家组成的。
M:个体历史的书写方法,依然需要的是捕捉线索,论证价值?但是您面对的是您所说的天马行空的多变的当代艺术,是临门一脚。
D:我们都喜欢按照自己的经验去预设,但最终在现场时你会发现只能随机应变,因为现场太丰富太具体了。我们就处于当下这个泥沙俱下、杂乱无章、充满不确定性、随时可能推倒重来的现场里。
M:您除了评论家的身份之外,还曾在一些重要的美术馆主持工作。以您个人的工作经验来说,民营美术馆应该做成一个专业性的、学术性的、深入性的、研究性的机构,还是更侧重于服务于大众,做一些当代艺术的普及与教化的工作?
D:当下是一个剧烈变动期,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在出现。前些年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不在意大众,因为有国外和国内大量的资金支持,一个展览来了百十个圈内人,获得的资金回报就已经很高了。现在,国外和国内的大收藏家和资本都从中国当代艺术界撤走了,做的展览没有他们买单了。这时还不在意大众的话,就难以为继了。过去是大收藏家给当代艺术买单,现在大家希望中产阶层和90后、00后的年轻人给当代艺术买单。过去是奢侈品店的模式,现在变成了电影院和游乐场的模式,希望一人一票、一人一件衍生品,积少成多来养活美术馆。所以我们看到那么多网红展。但美术馆毕竟是承担公共教育功能的非营利性的机构,不能整天做网红展,依然要做推动学术价值的项目。中国的美术馆缺乏基金会的长期资助,要想维持下去,只能几方面都兼顾,经过了这个转型期,有新的方向、模式出现的话,到时候再说。
 “潮流教父”KAWS的展览
“潮流教父”KAWS的展览
 草间弥生“我的一个梦”巡展
草间弥生“我的一个梦”巡展
M:在您看来这种新方向、新模式出现的趋势明朗吗?
D:我觉得最起码要等三五年。大资本,大收藏家集中进入的前提是要有足够吸引他们的富有学术价值的作品,作为一个中国当代艺术的观察者和在场者,我觉得目前没有集中出现这么多好作品。(采访时间:2019年4月19日)
|批评家杜曦云|

策展人,1978年生,2000年于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油画系,获学士学位。2006年于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史系,获硕士学位。曾任上海昊美术馆副馆长、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副馆长。
他的艺术观点著述于各类杂志和出版物,并曾创办和主编《艺术时代》等刊物。他曾参与组织、策划多个展览和项目,近期包括:联合构筑,苏州金鸡湖美术馆,2020;我与博伊斯·周啸虎,上海昊美术馆,2019;上海文件:匀速运动,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2019年;蒙塔达斯:亚洲礼仪,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2018年;今日之往昔:首届安仁双年展,2017年;走向未来:马德里·北京音乐潮,塞万提斯学院,2017年;萧条与供给:第三届南京国际美展,百家湖美术馆,2016年;北京·798诞生纪(2002-2006),宋庄美术馆,2016年。

 实体书影
实体书影